前言
为了马来亚的全民族解放而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当初整体组织陷入瘫痪后,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引起华侨之间掀起抗日救国(“国 ”指中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华侨抗日组织的前卫不断扩大了势力。关于这一动向,人们做了这样一些评价:“马共充分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国所引致的华侨之间产生的对中国的同情”、“马来亚的共产运动并非纯粹的共产运动,而是借用抗日反法西斯运动之名,实际上继续进行了共产运动”,即主张“利用”论、“伪装”论。但是,具有一定方向的组织上的急速膨胀往往会给组织本身的性质、路线带来很大的变化。如果领导人确信该方向是正确的,就更是如此。为此,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疑问:马共是否也通过利用救国运动,转换为特殊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组织?
以下将一边探索从马共成立至日军进犯期间的马共路线,一边就马共逐渐强调支援中国的必要性、而不重视马来亚的解放斗争的过程进行探讨,并考察当时的马共领导人是一些什么人物、领导人中有多少华侨?
一、战前马来亚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形态
1、南洋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论述,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治安当局的报告中出现是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运动的创始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主要通过在吉隆坡发行的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华文报纸《益群报》,劝说人们排除所有强权、支持绝对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及苏联,同时呼吁人们参加反对将山东省的德国权益让给日本、抵制日货、反对军阀等中国解放运动。1919年, “马来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Mal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成立,1925年会员约为50人。1925年之前,正面提出反英的暴力事件仅发生过1起,至1925年参加者大部分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根据谢文庆最近的研究,20世纪2O年代初期至3O年代后半期,斯尼弗里特(Hendrichus Sneevliet)、达尔梭诺(Raden Darsono)、阿利明(Mas AliminPrawirodirjo)、慕梭(Moeso)、丹•马拉卡(Tan Malaka)、苏丹•朱纳因(Sutan Djenain)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逃避印尼国内的镇压,或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指令,陆续进人马来亚,在马来人之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但是,正如丹•马拉卡1925年给同志的书信中所言,“马来人很保守,没有接受运动的余地。只有在华侨和印度人之间推广”,其目的并没有简单地得以实现。他们大部分人在短时间内就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6年初,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组成了被英国当局警戒为“马来亚最初的共产组织”的“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Nanyang Public Bodies’Union )。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孙文去世(1925年3月)l周年纪念活动和反外国反资本主义运动。该联合会的领导是由13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全部都是海南人(来自海南岛)。联合会不久便被迫解散,2年内临时委员有一半被捕。
1926 年5月,同样以海南人为中心组成了“南洋总工会”。到了1927年4月,该工会在马来亚、印尼、泰国、沙捞越已拥有42个支部,工会会员5000— 6000人,其大部分是海南人。而且据说一开始就处于中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系统)的全面指挥下。1926年,仍然以海南人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共青团于1925年1月26日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孙文逝世纪念日集会上,左派高喊着反英反帝口号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件和中国国内的国共分裂(4月)引致了马来亚国民党分裂—-脱离左派、组成“南洋共产党”。1928年1月以中共1927年1月至1928年初派遣的5名党员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党(关于这些领导人,将在后文叙述)。同年,接受共产国际1927年的指令,组成了“反帝大同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南洋共产党为了在马来人之间扩大影响力,在该组织内设置了马来部门,由阿利明、慕梭等领导。阿里(Ali Majid)等许多马来人加人了该组织,1929年阿里等3名马来人干部与南洋共产党的3名华侨领导人一起出席了“泛太平洋工会会议”(Pan— Pacific Trade Union Conference)(在上海召开)。此外,根据英国治安当局的文件,“南洋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中至少有5名马来人。但是,这些马来人领导人在1930 年之前大部分被捕。这时,对华侨共产主义者的取缔更加严厉,据说1928—1931年每年平均有1528人(马来亚国内的拘留者除外)被驱逐出境。好像对此加以补充似的,以海南人为主的许多中共党员又来到马来亚。后述的傅大庆也是其中1人。
南洋共产党向马来人扩大势力的愿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果,不仅大部分党员是亲中国的华侨,党本身也处于中国的领导下。据说,共产国际对这种事态表示担忧,决定解散该党并组成共产国际直辖的马来亚共产党(几乎同时也组成印度支那共产党)。
2、马来亚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论述,1930年4月中旬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或柔佛州武洛加色召开的南洋共产党第3次代表会议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大会。不仅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但由于马来人的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因此一个也没能参加。
据说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会议的胡志明一方面允许华侨领导马共,另一方面要求华侨领导人学习马来语等,以加深对马来人的理解,加强对马来人的影响。但是,根据谢文庆发现的英国治安当局文件,从会议记录可以确认有5名马来人出席了该会议。
杨进发根据对当时的有关人员的采访、成立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于4月29日被捕的事实(根据英国当局的记录。这一同时逮捕被称为“纳西穆街事件 ”{Nassim Road Incident},主张马共是“4月中旬”成立的,但马共本身将1930年4月30日作为建党日。而且,“马来亚革命之声”为纪念马共建党45 周年于1975年6月发表的“马来亚共产党简史”认为建党大会在瓜拉比拉召开。如果“4月中旬”是事实,为什么马共有必要说是4月30日?这是一个迷。根据原马共干部张明今所言,4月20日前后在武洛加色的会议上决定建党,并于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公布“4月30日正式成立”(1996年7月31日张氏给笔者的书信)。另外,台湾的张虎认为第3次代表大会的场所是在新加坡,并说召开日期是4月27日。
同年5月,南洋总工会改组为“马来亚总工会”;9月,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为 “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其势力来看,1930年马共党员约达到1500人,总工会会员达到10000—15000人,1931年约为10000人(共青团员人数不祥)。
马共一直致力于获得马来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林茂(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等,有许多马来人加入了该党的农民组织—— “农民同盟”(Peasants’Union)。1931年瓜拉比拉5名地区委员全是马来人。1932年5月,以7名马来籍干部(其中4人是印尼人)为中心,计划成立仅有马来人的政党“全马来党”(All—Malay Party)。由于干部被捕,计划失败了,但至1932年底,在马共各组织中,马来人及印度人达到了如下规模(马来人数不详,印度人不多):马共3O 人,马来亚共青团4O人,马来亚总工会1 000人,农民同盟100人。
也有人统计,1930年在加入马共各组织的11000人当中,马来人、印度人共计1170人。就是说,在初期的马共各组织中有10%左右是马来人。而且,其后没能在马来人之间扩大影响力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英国当局的全面镇压。因此,主要依靠华侨的这种马共路线的缺点不能仅归咎于党的领导层。
1931 年6月1日,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法国人杜克洛(Joseph Ducroux)、1929年初中共派来的傅大庆(均为马共领导)被捕。据说英国当局从杜克洛口中得到的情报传到了国民党政府,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此后至1933年8月共产国际断绝了与马共的联系。也许中共在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在 1931年召开的马共干部会上,决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反帝反封建斗争、马来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在这里,中国对马共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 1931年是发生“满洲事变” 的年份,马共积极地利用了华侨之间掀起的反日、救国情感。根据汉拉恩(Hanrahan)、布林梅尔(Brimmel1)的论述,新加坡华侨同年成立了抗日团体“华侨同盟”,马共也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抗日组织,而后篡夺了“华侨同盟”,并改称为“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但是,并没有其他资料记述类似于“华侨同盟”的组织,新加坡的史书记载,1931年中华总商会组织了“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但没有马共“篡夺了”该委员会的事实。另外,如上所述,“反帝大同盟 ”已于1928年在马来亚成立。
另一方面,战后不久的1946年1月在新加坡出版的马共宣传文件“南岛之春”叙述道:“1932年上半年党内出现了反党分子。他们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公然推行投降路线,进行出卖革命的反党行为”。进而,日军资料(《抗日共产党(含谋略的)事案状况表》。以下简称《状况表》)记载,“以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为契机,为了在马华侨的大团结、抵制日货、排日宣传及扩大党的势力,改称为‘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似乎根据这部文件写成的战时的日本出版物(筒井千寻《南方军政论》)也记述道:“1931年,新加坡的共产党员以此(满洲事变)为契机,呼吁‘在马华侨的大团结’并重新组成意味着反法西斯主义的‘马来亚反帝大同盟’这一政党,以往的南洋共产党也包含在其中并消失了”。
在战后发表的马共正史中完全没有言及“反帝大同盟”,但根据当时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参加马来亚左翼运动的马宁所言,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不仅仅华侨,还集中了马来人、印度人,旨在解放马来亚全民族。马宁1932年在马共宣传部长、该大同盟负责人邬志豪的请求下当上了大同盟宣传部长,但因邬主张“工人、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革命是必要的,工农斗争是不必要的”,被当作反党分子处以死刑。
“ 南岛之春”所谴责的“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似乎就是“反帝大同盟”,但中国的出版物和回到中国的原马共相关人员近年来的回忆录都对当时的“反帝大同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看来,很难认为“南岛之春”谴责了“反帝大同盟”。而且如上所述,设立时间也有问题。“马共大同盟”的真实情况至今仍不明朗。不过,争论点在于是以华侨为中心进行抗日还是动员“全民族”进行马来亚解放斗争?或是重视共产国际还是重视中共?在肃清“投降主义者”之后,于1932年召开了马共第3次代表大会,会上改选了中央委员,同时通过了如下l2项革命纲领:
(1)驱逐英帝国主义,推翻其傀儡——酋长、苏丹、地主、买办资本家的统治。
(2)没收帝国主义者的银行等一切反革命财产。
(3)把帝国主义者、酋长、苏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庄园分配给农民、农场工人、革命战士。
(4)解放马来亚的民族、社会,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
(5)废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经济。
(6)实施8小时工作制等,以保护工人。
(7)争取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对一切反动宗教。
(9)以各奎国语实行无偿教育。
(1O)杜绝剥削。
(11)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2)保卫苏联,支持中国、印度的革命,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
保卫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口号应该是根据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会的“关于中共的任务的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中国反革命<支援国民党,)或1932年9月共产国际第12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总会提纲(为了保卫苏联、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指示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提出的。汉拉恩认为“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局重组后,立即指示马共进行反英斗争”,但从1932年的纲领开头主张“反英”的情况来看,在东方局重新开始活动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概是通过某种渠道传达给马共的。
在党内反对派被清除、斯大林率领的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业已确立的当时,共产国际传达给各国共产党的通知是不允许有异议的至高无上的指令。就马共来看,不能确定1932年是否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但1933年8月以后的确是有联系的。如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将保卫苏联作为自己的目的一样,在马共当中,共产国际所主张的“保卫中国”与华侨党员所具有的中国归属意识产生了共鸣,展开了独特的自己的运动。
在12项纲领中的前面提出了与英帝的斗争,那是为了“保卫苏中”。 “反动宗教”具体说来大概指回教,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充分考虑到要获得马来人的支持。此外,从“本国语”的表现来看,似乎马共依然有着将中国视为奎且的倾向。接着,根据英国当局所获得的情报,1933年9月中共中央向马共中央发出了“集中各族代表设立‘反帝大同盟’”的指示,1934年6月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发出了建立全民族劳动阶级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的指示,1935年6月马共中央为了促进马来人、华侨、印度人3个民族的团结,设立了由各族各1名代表组成的“ 团结委员会”(Unification Committee),在1936年9月的第5次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重新确认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和扩大,同年l0月在团结委员会下设立了“ 马来亚各民族解放同盟” (Malayan Racial Emancipation)。上述的《状况表》中记载,“至1934年,集结在马华侨、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谋求大团结,以期扩大党的势力,并改称为马来亚各族解放大同盟。” 在包括“南岛之春”的马共正史中没有关于“各民族解放(大)同盟”的记述。在当时的口号中新添了“反法西斯”。但其中有“与中共、苏联联合,以期保卫中国、阻止侵略中国”的记载,仍然存在着对中国的特别定位。
1932 年的反英纲领出台后,反英斗争一时高涨,但在1935年7—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提出了“人民战线”战术后,主张反英武装斗争的一派被清除了。他们在“南岛之春”中谴责说,“他们想把马来亚的劳动大众永远当作英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奴隶”(第9页)。此外,马共代表伍天旺提交给1947年在伦敦召开的“英帝国共产党会议”(British Empire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的文件“马来亚的共产党”就1936年的分派谴责说,“主张停止罢工、战斗的工人潜入地下,反对半公开劳动大众组织。指责党的厦童统战政策,将党的路线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否定反帝斗争中的党的领导性、扰乱党的团结的反动派、帝国主义的爪牙、‘左倾机会主义者”’。分析了这份文件的谢文庆推断,“分派只不过是要暂时避免与当局的冲突,以保存势力。从1935年l2月至1936年3月,两名党委员长连续被捕,镇压异常严厉,还发生了几起党的干部遭到暗杀的事件,为此党内便疑心生暗鬼”。但是,从1934年底或1935年被英国当局作为间谍派入马共的莱特当时因解决党内对立而崭露头角(后述)的情况看,很难认为反对派就是对英绥靖派。谢文庆所引用的英国当局的文件也认为主流派是稳健派,反对派是强硬派。
关于1935年和1936年的党内对立和“邬炽夫事件”,原马共干部张明今指出:
马共初期并不是很严密的组织,经常发生党员和干部被捕事件,因路线、政策、观点不同而争论不休。中央领导人频繁更换,中央书记(总书记)也是每年一换。 邬炽夫(邬志豪的别名)认为,马来亚的工农大众的认识还很肤浅,因此首先应该发动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掀起像中国的‘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然后再深入工农大众中动员,并批评了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对此,党中央的主流派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必须把深入工厂、领导工人罢工、动员工人作为主要任务。 1935年,英当局公布“华侨登记法”,学生起来反对。继邬炽夫之后当上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的陈子彬向党中央建议配合学生的行动,进行罢课、罢工、商店歇业、劳动节等革命纪念日的街头游行、集会、演讲等,但不仅未被采纳,而且被批评为“左倾幼稚病”。 7
本来党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争论是受到允许的,也是正常的,但莱特假冒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混入马共组织(1935年前半期)、成为党中央常任委员(海南人)幕后的秘密顾问后,就不正常了。党内斗争日益激化,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以第三国际假代表为中心的中央委员多数派(海南人)说“停止争论,进入工厂”,另一方面,党中央宣传部长邬炽夫和中央书记刘登乘看穿中央有问题(但他们不知道莱特是混入党内的间谍),想邀请常任委员以外的干部马宁、陈子彬等“反帝大同盟”领导人组成别的中央常委。邬炽夫和刘登乘同是广东省大埔出身的客家,因此当时传闻马共分裂为海南帮和客家帮等。间谍莱特在幕后操纵海南人,挑拨离间,说“党内出现反对派,要斗争到底”,并进行残酷的暗杀,向英国“犯罪调查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ID)告密〔为此核心干部遭到逮捕〕等,而马宁、陈子彬(同是福建人)不知内部斗争的本质,更不清楚莱特的这些情况。陈子彬〔1993年在广州居住〕说,“{1935年下半年}邬对马说,‘马共中央被海南人掌握,都成为海共了。他们的水平很低。我们另立党中央吧’。邬只想建立 ‘中央’,并没有召集人员建立其他组织。但莱特向多数派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肃清反对派’的计划,让其采纳了‘常委必须深入基层(工人当中)指导工人的罢工 ’的决议,并决定将邬调往马六甲。邬乘火车抵达淡边(Tampin,森美兰州),从那里骑自行车往马六甲途中,潜伏在路边的马共党员(海南人)用铁锹打死了他。海峡时报立即报道了这一事件,CID为了掩盖莱特的阴谋,麻痹党员的神经,将此说成了桃色事件。
暗杀的传闻四起,我便追问中央领导同志(海南人),他们看无法隐瞒,便把真相告诉了我。暗杀意见不同者的做法与我的思想相距甚远。不久,南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部长刘××警告说,‘不能忘记这个教训’。这时,又发生了几起失踪、被捕、暗杀事件,借这个机会,我辞去了大同盟秘书长之职,并退了党”。
马来亚红色总工会的负责人老黄、即亚三因没有实行暗杀邬的计划,被开除出党,回到中国后,在海南岛的海口被暗杀了。其后,党内再也没有敢说邬暗杀事件的人。邬遭暗杀后,中央书记刘登承也险遭暗算,便逃回故乡大埔。1936年夏天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张明今于1937年前往南洋)。 1938年我在森美兰工作时,一位老党员在淡边附近的橡胶园内透露说,‘这里埋着反对派的领导人’。其他情况没能打听到。
注:〔 〕内是张明今自己的补充。以下〔 〕内的内容也并非笔者所为,而是证人或原文献的补充。
邬炽夫暗杀事件符合谢文庆所指出的1935—1936年的情况,马共相关人员在近年出版的书中也认为是1936年发生的,因此马宁的1932年之说大概是错误的。但是,马宁于1931年2月一1934年4月在马来亚居住后,在1941年初之前回到中国(参照资料“马来亚共产党原干部会见记),发生暗杀事件时并不在马来亚。也许张明今将他与其他人物混为一谈了。
总之,由此可以了解到把有才能的干部接二连三地出卖给日军的莱特的手段已初露端倪。他并非调停两派的对立而崭露头角,而是由于主谋清除反对派而崭露头角的。无论两派的对立源于什么,对莱特及其“主子”英国来说,邬炽夫派、即反英派都是危险的存在。对他们进行压制与共产国际为了推行反法西斯运动而抑制反英斗争的这一时期的方针是一致的。
在共产国际要求马共的两个主要事项中,“反英”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苏联政策的转变,而另一个“全民族的团结”由于马来亚国内的情况而没有持续下去。如前所述, “团结委员会” 由各民族的1名代表组成,“各民族解放(大)同盟”也由2名马来人、2名印度人所加入的“委员会”领导。此外,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苏丹•朱纳因是马共中央委员、各民族解放(大)同盟委员。据说印尼共产党原委员长萨乔蒂(Sajoeti)也于1934年9月进入新加坡,直到1935年7月遭到逮捕、驱逐,一直在马来人之间进行秘密活动。但是,由于当局的严酷镇压,马来人的活动日渐衰退。这种事态与华侨的抗日热情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而迅速高涨、以及利用中华民族主义成为了扩大势力的最好战术一起促使马共暂不实行共产国际的“全民族”路线,而重新确立了华侨路线。 据说,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1937年8月)后,于1938年2月举行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的“拥护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会上提出了下面这些口号。
(1)清除一切掠夺者及托洛茨基分子;
(2)打倒威胁国际和平的日本法西斯;
(3)取得支那民族的解放与自由;
(4)抵制日货。
将掠夺者和托洛茨基列在一起是斯大林推广的想法,且不去考虑。这里重要的是第3点。
1938年4月召开的马共中央常任委员会对形势做了如下分析:
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和平势力的斗争日趋激化。尤其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加强对中国的进攻,对马来亚的安全带来了威胁,激起了马来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气势。而且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也加强了马来亚人民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信念。特别是占总人口一半的华侨与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家乡的关系和观念极为深厚,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祖国的反感更加强烈。
该常任委员会所采纳的纲领主张建立包括各民族、党派、阶层的“马来亚人民统一战线”,共同制裁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改善军事行政(马来亚士兵和英国士兵的平等待遇等),要求英政府禁止为日本法西斯筹集武器、资材、粮食,拥护苏联等,同时在第七项中提出“援助中国的自卫战争,停止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运输、开采铁矿、进行橡胶采液及其他作业,实行抵制日货运动,募集义捐款,组织慰劳队和国际义勇军,积极援助中华民族将日本法西斯驱逐出中国 ”。进而,在同年7月的马共第4次执行委员会上采纳的斗争方针是,要求英政府明确反法西斯,“为了加强华侨统一战线,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解决华侨劳资关系”。
7月30日,马共的外围团体“马来亚抗敌后援会”(抗援会。后述)的5名常任委员(黄)耶鲁、洪涛、吴天、(戴)英郎、(王)厌之联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具有下列内容的公开宣言:
(1) 认为大英帝国是共同反法西斯侵略的我们生国的亲善友邦。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和治安上的困难,我们拥护当地政府在中日抗战中采取中立的态度,日本在侵略、蹂躏我们中国,希望当地政府理解我们的合法的救亡活动。
(2) 拥护上层侨领的赈筹义举,愿意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救亡工作。
(3) 抗日高于一切,在劳资问题上,不随便罢工,致力于和平解决。资方为求增加生产,以充实国力,尤应尽可能改善劳工生活,并予劳方以从事救国工作的自由。
(4) 全马同胞根据蒋委员长的指导,以及中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抗战救国大纲,合力统一救国信仰、救国组织和救国行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巩固和扩大马华救亡统一战线。马华180万侨胞不分阶层、帮派、地区,团结起来成为祖国最高当局的后盾。在开展统一行动时,各地筹赈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这是将先前采纳的马共的“斗争方针”加以具体化的内容,由此可知抗援会根据马共的方针实施行动,对马共和抗援会来说支援中国抗日斗争已是最大的目的。
1939 年4月初的马共第六次扩大中央委员会被认为是马共“从秘密的处境到具有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的转折点”。该委员会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帝在马来亚一方面加强剥削,而在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则产生了动摇。在反法西斯方面与英帝合作,人民的力量仍显不足,因此党必须通过结成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获得民主权利的斗争,来组织群众”,制定了10项“为了获得民主权利的斗争目标”。在第9项中写有“支援中华民国的民族自卫战”。在同时采纳的“新政策”中认为还没有力量推翻英帝,因此将“获得民主,保障和平”作为党的任务,并随处可见“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难以决定当前是与日本法西斯斗争还是与英帝斗争的迹象。此外,虽然号召各民族的团结,但“中国的民族自卫战”这一表现如实地反映了马共强烈的亲中国倾向
在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缔结(1939年8月)后不久的1939年9月,马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反战决议”,号召人们反对英帝借口欧洲战加强剥削,进行反战斗争。这一路线转换是由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强令各国共产党停止反法西斯斗争,并未结合马来亚的形势所采取的措施。
接着,1940年2月,马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实施第6次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如下决定:
华侨必须以祖国的抗战为中心。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坚持抗战使全马华侨的上中下各阶层朝向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斗争目标。为此,如果反日、反汉奸是华侨当前斗争的基本目标,马华(马来亚华侨)抗日统一战线能够得到普遍的正确的发展,那么这同时也会带有反帝的性质。马来亚华侨当前的斗争没有直接以英帝为主要对象,因此华侨在反帝统一战线中没能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将来的发展中,将会随着各民族解放的热潮转为主导地位。同时,号召马来亚(马来之误)民族进行民族独立运动。他们的斗争对象就是压迫、剥削他们的英帝。同样也号召印度民族与英帝作斗争,响应祖国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热烈支援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个决定将会纠正无视各民族特殊性的以往的缺点。
这完全推翻了先前的“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理念,“根据现实情况”,分开进行斗争,即:华侨支援“祖国”中国的抗日战争”,马来人在马来亚进行反英斗争,印度人支援“祖国”印度的反英斗争。这里说“抗日救国”时,“国”不是马来亚,而是指中国,而“汉奸”一词则表明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成为反汉奸斗争对象的是与中国关系淡薄的马来亚出生的华侨(杏吝),当然“ 受害者主要是吝吝华侨”。可以说马共的亲中国至此达到了颠峰。
此外,根据1940年3月英当局查收的马共文件,马共当时的目的是妨碍马来亚政府机关、动摇亚洲籍民众和英国籍民众的士气、煽动人们怨恨英帝、以罢工破坏马来亚经济。尽管党中央把方针转为重视抗日战争,但现实中反英斗争依然以相当大的规模展开着。
日德意防共协定缔结(1940年9月)之前,党中央制定了如下“华侨救运策略方针”(华侨救国运动战术方针):
(1)华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利用所有公开手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取得救国运动的合法性。打倒日帝及汪(精卫,下同)派汉奸,为祖国抗战的胜利而斗争。
(2)华侨工人的罢工应该停止。今后,罢工的对象应该集中于帝国主义的咽喉及汉奸汪派资本家。
(3)抗援会(1937年8月成立)由于妨碍救国运动的合法性,因此需解散后重组为符合大众觉悟的各种抗日组织。
(4)为了改善救国运动的环境,必须停止反英活动。应该指导自发的反增税运动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在援英运动中保持中立。
这一方针是根据1940年7月或同年9月由中共送达的国共合作、停止反英斗争的指令制定的。在这里,马共的眼睛也完全朝向了“祖国”中国。停止反英斗争并非马来亚国内形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为了加强“救国”(中国)所需要的。
根据回到中国的华侨近年来归纳的记录《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抗援会是响应中共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当地的革命组织(即马共)的领导下成立的半公开的组织,最高领导人是戴英浪、王炎之、粘文华等马共干部(如后文所述,3人当中王、粘也是中共党员),会员达2O一4O 万人。但是,1940年2月马共中执委为了合法地继续救国活动,决定解散抗援会,建立新的各种抗日组织,并继承其活动。顺便提一下,日本的战时报告书也认为中共组织了“马来亚各界抗敌抗援总会”。此外,根据上述的《选辑》,以往被认为是国民党派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部队”(简称“民先”)也是在1937年“9.18”事件6周年纪念日根据中共的指导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秘密组织,1939年以后马共内部增加了该党党员。《选辑》还叙述到,“民先”顽固地坚持不介入马来亚的革命斗争,但因遭到英国当局的严酷镇压 (干部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进行间谍活动等)而受挫。
可见拥有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抗日组织与其说在马共的领导下,不如说是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可以说,这些事实显示了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之深和马共亲中国之强烈的背景。
1941年6月德苏战争开始,7月,马共第7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召开,决定建立马来亚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中国,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此,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被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而暂不作为当前的战术目标。
关于是否应该将英国作为主要敌人,据说短期内经常推翻相关决定,这种混乱状态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日军进犯时,街上“彻底抗战”(援英)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英)的传单竞混杂在一起。
如上所述,日军进犯前的马共路线的变化和动摇不用说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斯大林体制的确立而使马共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一样成为了共产国际(直接地说是苏联)的外交棋子之一。但是,由于极强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马来亚的现实斗争受到了忽视,为此很容易遵循其他国家(共产国际或中共)的指令,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二、战前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1.南洋共产党
关于南洋共产党(以下简称“南共”)及初期的马共领导人,除了认为1925年在广东接受丹•马拉卡的邀请进入马来亚、1931年6月与法国共产主义者杜克洛一起被英国当局逮捕的Fu Tai Keng(Fu Ta Ching)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但近年来杨进发根据对居住在中国的原有关人员的采访调查等,做了接近整体状况的珍贵的研究。另外,Fu Tai Keng的汉字在战时的日军资料中写成“符大经”,在中文资料中是傅大庆(Fu Da Qing),杨进发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本文拟使用傅大庆这个名字。
以下主要根据杨进发的研究记述一下领导人的情况:
中共派到新加坡的密使——5名中共党员作为党总委员(General Committee)担任了核心领导。
潘先甲于1926年进入马来亚,负责设立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洋总工会后,1927年临时回国,后又被派遣到马来亚。
杨匏安在留学日本后,于1921年在广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1月逃到新加坡。南共成立后自愿回国,但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处死。他的日语也很好。
‘张洪成、即黄德才。儿时进入马来亚,1919年被英国当局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当作危险分子。1920年赴爪哇领导劳工运动,1924年被荷兰当局强制遣送回中国。1925年在福州加入中共。他在南共除了担任书记、总委员外,还担任军事委员。
张玉楷在广州起义时越狱,2月因策划暗杀访欧途中拐到该地的国民党干部伍朝枢而被捕,3月被判终身监禁。
关于“在当地参加”的8个人,其特征是全体成员都是海南人。但是,本人出生于海南、后来前往马来亚的只有王月波和詹行祥,其他6人也有可能出生于马来亚,但杨进发未作任何叙述。马业炳和王月波在20年代都是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他们通晓马来语,负责与阿里(Ali Majid)、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等马来籍领导人联系,并于1929年8月与另一名华侨、阿里等3名马来人一起作为马来亚代表出席了前述的上海“泛太平洋工会会议”。此外,1928年1—3月许多总委员或被捕或回国后,詹、马、陈绍仁与黄默涵一起被任命为新的总委员(杨留任)。黄出生于海南岛,后前往马来亚(时期不详),1929年10月被强制遣送回中国。1931年4月又与杜克洛一起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往新加坡,但与杜克洛一起被捕(英国治安当局事前得到情报,人境后不断严密监视其行动和交友关系),1932年死于狱中。
关于这一时期马来亚共产运动领导人中海南人特别多的原因,杨进发指出了以下几点:
(1)当时的海南岛热心于教育,夜校特别发达(在马来亚,夜校也成为了运动的重要据点)。
(2)1925年以来,海南处于国民党左派的统治之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将海南人密使送人马来亚。
(3)由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与广州起义失败,几千名海南人共产主义者到马来亚避难。 (4)他们是华侨社会的少数派,其内部很团结。
(5)他们经济、社会地位很低,大部分是下层工人。
(6)有家庭的人很少,容易活动。
(7)留学黄埔军校的人很多。
顺便提一下,根据台湾研究人员的研究,国民党马来亚支部从1912年成立到20年代末,其大部分党员是海南岛出身的工人。其原因有,海南人是热心的孙文支持者,大多数是工人,他们支持孙文的反商人主张(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103—106页)。
从1929年6月到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南共最后的3名常任委员有着下列这些简历:
吴清于1921年在海南岛海口参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人黄埔军校,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前往新加坡,担任南共书记,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成为该党组织部长,但同月29日被捕。被判2年徒刑(实际服刑大概只有1年)后被遣送回广州,在广州被国民党政府处死。
傅大庆生于江西省,1924年留学莫斯科,毕业于孙逸仙大学,回到广东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1927年底参加广州起义后,1928年临时在新加坡避难。1929年初又前往新加坡,就任南共宣传部长,接着担任马共宣传部长。1931年6月,与杜克洛一起被捕,1932年被强制遣送回国。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北京被日军处死。
傅大庆
林庆允是海南出身的工人,南共中央常任委员,在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任中央执行委员,首任马共书记黎光远被捕后任该党书记。1931年6月1日杜克洛、傅大庆被捕时由于身在槟城逃过一劫,以后仍在槟城活动,并辞去了书记职务。
以上是南共主要领导人的简介。他们都是中国出身、尤其海南出身者较多,最高干部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后有时以临时避难的形式进入马来亚(主要是新加坡)等。他们的目的之一是加强革命运动的实施。说起来,其必然的趋势是更加重视扩大对中国抗日运动的支持、以及国共对立时扩大对中共的支持。
2.马来亚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研究,建党大会时的代表有20人,11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常任委员(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组成)。11名中央执行委员的简历如下所述。这里将对各位领导人稍加详细的探讨:
苏丹•朱纳因、即阿里如前所述是为了做马来人的工作而加入马共的印尼共产党员,作为马共中央委员只是在英国当局的文件中出现。据笔者所见,以前在马共本身的文件中并未出现这个名字。但在最近出版的马共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有以下这些记述:印尼大革命失败(1926年)后,逃到了森美兰州,在马来人中进行秘密活动。战后成为马共森美兰州办事处的1名代表,也是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该州支部负责人,但后来被遣送回印尼,受到了苏加诺的欢迎。1953年印尼共产党(PKI)主席艾地在莫斯科与马共人员会面时,马共方面告诉他已恢复了朱纳因的党籍,印尼共产党也在主席回国后恢复了其党籍。50年代末病逝。 (单汝洪《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 第163、195页)
前面已叙述到,1936年邬炽夫作为党内反对派被肃清。邬于1900年代中期生于广东大埔(以客家的家乡闻名),1925年加入共青团,接着加入中共,1927年的“4.12政变”(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后前往马来亚,加入南共、马共。1931年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就任该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马来亚反帝大同盟”筹备处负责人(秘书)。
陈子彬1910年生于福建龙岩,1929年前往槟城,以林岩、一萍等笔名进行了文艺活动。1935年至1938年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在彭亨、森美兰两州流浪(这也许是指脱离马共后的不安处境)。根据张明今所言,他接替邬成为了“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但因邬被害事件退党,其后回到中国。根据马仑所言,他于1940年回国,原打算去抗战的中心“西北高原”,但却在重庆停留了6年。战后, 1946年又来到马来亚,为《现代周刊》(槟城的左派杂志)写稿,但1949年最终还是回国了。 b 蔡白云生于新加坡的福建籍商人之家,1937年初由于抗日运动被英国当局逮捕,拘留半年后,同年底率领一队青年前往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工作。1938年8月作为中共“海外工作团”副团长奔赴印支各国。1940年暂时前往香港,在中共华南分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43年重返印度支那进行抗日运动。在战后的1946年,他在西贡对华侨进行中共的宣传工作时病死。1984年被中国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越南华侨烈士)。
蔡长青{蔡白云}
刘登乘因与邬炽夫结盟,事件后便被革除书记之职,逃回故乡大埔,改名为刘德和,并加入了中共。但由于莱特领导下的马共中央以临阵逃跑罪永久地剥夺了刘的党籍,并把此事通报给中共,中共也在1940年前后将刘除名。其后,刘在广西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死于狱中。
林德(“林德”是台湾出版的书籍中的音译)也没有在马共本身的文件中出现。无论是共产国际派遣这一点,或是派遣的时期,还是会数学或国语这一点,都与莱特相像,但真相至今仍然不祥。
关于莱特,已经有很多记载。一般说法是,他1934年底来到马来亚,1935年进入马共领导班子,1939年就任总书记。马共本身也认为,“1935年他利用党内的混乱,伪装成第三国际的代表潜人党内,1939年篡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1966年有人发表了“1931年从新加坡码头工人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青年领导人,马共中央与之接触时,他称是第三国际派遣的莱特。以后他便迅速地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之说,但未能推翻一般说法。张明今认为莱特是 1937年成为实际上的党的领导人的。马来亚占领期间的日方资料将战前马共最高领导人莱特记为黄绍东(越南语为Hoang Thieu Dong),但研究马共的最基本的文献汉拉恩的著作中仅有简单的记载,说黄绍东是“3O年代初期的领导人”,不是把黄绍东,而是把Huang Na Lu作为莱特的别名。Huang Na Lu应该是汉语或日语文件的翻译者黄耶鲁(Huang Yeh Lu.Huang Ya Lu)的“耶”误译为“那”的结果所产生的名字。显然莱特=Huang Na Lu之说是双重错误。
莱特
马共战后的机关报《民声报》(1948年3月6日)就战前被强制遣送回国的马共领导人,列举了郭戈奇、王厌之、戴隐郎、粘文华的名字。此外,前述的《选辑》认为戴、王、粘3人就是抗援会的中央领导人。以下以这些领导人为中心探讨一下他们的简历。
根据当时的日方文件,王炎之(王厌之的别名)、粘文华、黄耶鲁、辜俊英于1937年7月由中共派遣进入马来亚,但有人认为王、粘、黄进入马来亚的时间实际上比这一时间要早1—3年。
王炎之——本名是王宣化,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14年前往菲律宾,1917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商学系,1921年回国,1923年前往新加坡设立了“南洋影片公司”(影片为相片之意),1928—1930年留学于东京大学(因此能读写日语),1931年回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又前往马来亚,在霹雳州州府怡保担任华文报纸《中华晨报》的总编,之后转移到新加坡领导抗援会。1938年8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同月被强制遣送回国。自193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54—1980年)、全国归侨联合会(侨联)委员(1956—1980年)、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等。日方资料认为马来亚的王炎之是“最恶劣的抗日团体的首领”。
粘文华——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30年加入中共,1935年成为了泉州特别支部书记。1935年6月前往新加坡,在抗援会担任“党团”书记。1938年与王炎之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国。以后在泉州等地继续进行抗日运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任厦门市工委书记、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等职。这里所说的“ 党团”不知系指何意,但如后文所述,粘文华并没有成为马共书记,因此大概是指抗援会内的马共机关。总之,可以想见粘在马共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方资料,粘是“隶属于星州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暴力集团的头领”。
粘文华
戴隐郎——即戴英郎,他生于吉隆坡,20年代中期留学于上海美术学院,30年代前半期回国,作为作家和画家在“星州(新加坡)业余话剧团”等工作,同时成为了抗援会的最高负责人。1940年2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同年5月被强制遣送到中国。其后以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份活动,后来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86年在杭州去世。
郭戈奇——近年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根据该回忆录,郭在1940年以前就很想奔赴延安,但组织(大概指马共)要求他继续在马来亚斗争。通过与先去延安的同志通信,更加坚定了他去延安的决心。1939年冬被英国当局逮捕,受到半年监禁后,被强制驱逐出境。1940年6月前往香港,同年底抵达延安。
关于辜俊英——在前述的《选辑》中也记载他作为“抗援会”负责人、新加坡抗援会负责人之一1938年8月与王、粘、苏棠影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国,因此大概是马共领导人之一,但具体情况不祥。根据日方资料,辜被强制遣送回国后,在福建被国民党政府枪杀。
根据前述的《选辑》,苏棠影是抗援会的负责人,也参加星州业余话剧社。根据日方资料,他是“民先”的“隐蔽的领导人”。
1938年8~10日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辜俊英的逮捕和强制遣返当时被称为“四君子事件”。
黄耶鲁——(19 13一)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作为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进入厦门大学的当年,发生了“9.18事变”,便投身救国活动。黄本身和中国方面的资料都说黄是中共党员,他参加“反帝大同盟”是显而易见的,逃亡国外(1935年)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经由缅甸、米里(沙捞越),1936年进入新加坡,一边从事教职,一边参加左翼活动,主要担当文化工作。1938年加入马共,同年7月在马来亚抗敌后援总会正式成立大会(如前所述,抗援会应该是在1937年8月成立的,但1938年7月以前只是各州的组织)被选为5人常务委员之一。同年秋天,成为槟城的《光华日报》记者,领导马来亚北部的抗援会。1941年5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在日军南下马来半岛的同年12月被释放,担任促进华侨义勇军成立的工作。日方资料记载,“他是报纸杂志的撰稿人,是新加坡文化界异常活跃的分子”,“在马共中央干部中最有知识”。
在与黄耶鲁一起发表“我们的态度”的4名抗援会常任委员中,英郎(戴隐郎)、厌之(王炎之)已在前面叙述过。洪涛是辜俊英的别名。吴天本名是洪为济,1913年生于江苏省。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但因“9.18事变”后参加救国活动被开除学籍。1935年留学日本,1936年进入马来亚,在新加坡、森美兰担任教员,同时以“叶尼”的笔名执笔了许多抗日戏曲和评论,成为了抗日文化活动(尤其是演剧活动)的一名中心人物。1939年回到中国后,作为剧作家、演员活跃于上海,晚年移居广州,1989年去世。前述的《选辑》记载,“1939年吴天等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被驱逐出境,抗日救国运动受到了打击”。
杨少民(肖明)——作为1939年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老革命家出现在《选辑》的战前马六甲抗日运动的回忆录中(第480—483页).前后的经历不祥。小中、林江石在开战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他们同样出生于中国,幼年时期前往马来亚。
如上所述,30年代后半期,“大东亚战争”开始前的马共领导人大部分出生于中国,即使是马来亚出生,也是留学中国的归国者(戴隐郎)。其中,王炎之、粘文华在进人马来亚前就已经是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可见是中共为领导马共而派遣的。郭戈奇不知是生于马来亚还是中国,但他自己说,他一面在马来亚活动,一面很早就热切希望前往延安。而且,受到英国当局逮捕、强制遣返的原因都是过激的抗日运动(英国害怕日英关系恶化)。3O年代中期的领导人(马共书记)蔡白云生于新加坡,但难以抑制救济祖国的热情,1938年初背着英国当局秘密前往香港,随后进入延安。马共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在此处也显现无遗。
通过对杨进发的研究加以归纳,1930年建党以来的马共书记有以下几位。
(1)黎光远 1930年4月中旬~4月29日
(2)林庆允 1930年5月~1931年5月
(3)符鸿纪 1931年6月~?
(4)蔡白云 1936年~?
(5)莱特 1939年~1947年
另一方面,根据张明今所言,历代书记有如下这些人。
(1)林庆允
(2)闵竞平
(3)刘秉义
(4)蔡白云
(5)刘登乘? ~1935年中期
(6)欧往修1935~1936年
(7)莱特1939—1947年
两者之间的名字和时期有相当大的出入,也有与前述的邬炽夫事件(1936年)前后矛盾的一面,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留作今后的课题。但在莱特之前,书记只不过是领导人之一,几乎每年都换,而在1939年莱特成为中央“总书记”以后,其地位不可侵犯,独裁体制逐步确立,这些情况是千真万确的。
附:作者简介
原不二夫(Hara Fujio):1943年生于日本长野县。1967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年进入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工作。1972年-1974年作为海外派遣员进入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1987年-1989年以海外调查员身份被派遣进入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担任研究员。1992年-1994年又以高级海外研究员身份回到马来亚大学担任经济与行政学院研究员。1999年离开亚洲经济研究所,出任名古屋南山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 原不二夫通晓日文、英文、中文和马来文。在亚洲经济研究所任职时期是担任地域研究部门主任研究员(教授),曾三次被派遣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作实地考察研究工作。为了要了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合作,他于1993年春到中国汕头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所及海南大学人文科学院作访问研究。 他主要研究课题是马来西亚的日本移民和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著作颇丰,以日本文撰写的编著有《英属马来亚之日本人》,《东南亚的华侨与中国:中国归属意识华人意识》和《马来西亚抗日文学选》等六种。以英文撰写或编著的著作有四种。1991年与崔贵强合著《新加坡亲中国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一书。在马来亚大学担任研究员时,曾邀请马来西亚多位学者撰写有关布米普特拉和华人企业的问题。1993年主编《马来西亚商业集团的形成和重组》,1993年又主编《马来西亚布米普特拉企业和马来人华人经济合作》一书。1997年又出版《马来亚华人与中国: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7》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十余篇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论文。1998年12月以中文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一文刊登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二期。
原不二夫被认为是日本研究华侨华人的杰出学者,是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研究的专家。
“Skepticism cannot be revolutionary, even though it speaks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 Raymond Aron
Pls Click To Support This Blog,TQ!
請支持原創~讓鬥爭持續下去!
《逆流世代》屬非盈利,幾年來不斷勤於發表大馬政治時事評論,免費供網友們閱讀。請給予支持,樂捐些稿酬於部落客,信用卡與Paypal都OK,有多少就多少~再次感謝您熱心的支持。
Donations Are Welcome,to keep Arus Lawan's blogger continue his passion & struggle,Thanks 4 your support.
若無Paypal帳號,您可以透過銀行或網絡轉帳進行匯款,請聯繫:
If you don't owned a Paypal account,you can pay via bank tranfer or online banking,pls contact 4 further details:
kawasaki918ken@yahoo.com.tw
2010年7月27日星期二
能否给泰益一只“飞鞋”?
“白毛”泰益玛目的轶事相信许多人都听闻过,但西马人要真懂远在东马对岸的砂拉越的这位传奇人物,我想从当地人嘴里便能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丑事。然而他名声那么臭却还能执政那么久,甚至比马哈迪早登位,更何况马哈迪早就退位了。这是为何?大权独揽在握十几二十年,加上山高皇帝远,国阵大可则装作看不见,只要能稳住它的执政地位就好。
泰益独揽的土保党,美其名保护土著,实着在侵犯当地土著权利。砂拉越的许多树林被加以滥伐、天然资源被非法盗取,泰益家族、朋党乐于坐视不管,反正有的是从中捞取庞大的利润。无法无天之级已不在话下,泰益确实不输给早期统治砂拉越的“白种人王朝”,如今“白毛”集团掌控着砂拉越的实权,其剥削的力道相反更甚于那些殖民主义者的白种人;也因此,所有砂拉越的资源、产业等仿佛归他所管,你姑且可说泰益是砂拉越的“土著国王”,很明显原住民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还会失去更多的祖灵之地,任凭那些非法伐木者随意宰割。一些消息指出泰益家族在海外有很多资产,这有什么好出奇的?那些执政党的那些资深老大哥有哪些在海外听说没有房地产的?连前首相马哈迪在海外据说也有别墅,这确实不奇怪。在西马这里是一党独大(有待改变),而砂拉越则是泰益的家天下。莫怪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能运转那么多贪腐而来的资金,而陈水扁如今被法律所制裁,在牢里坐监了,而马来西亚的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客呢?谁来治理他们?
Bruno Manser基金会指出砂拉越的处女林如今仅剩下3%,相比较早前10%上下的数据少了一大撮,砂拉越森林几乎快要变成“botak”的状态了,然而这些不公谁来理会?原住民不懂得抗争吗?Bruno Manser基金会有许多主流媒体无法出示的证据,例如1993年本南族男孩被警察所行使的非法暴力杀害;2007年愤怒的本南族人得不到政府的回应,设下路障阻碍伐木工厂出入,而警察却开枪威慑示威者,把路障的树木锯断并焚毁。近几个月更是传出了伐木工人进入本南族部落为所欲为、禽兽不如的违反人道、践踏原住民之行径,而纳吉仅是装模作样登门拜访,设立了一个所谓委员会调查此事,问题是,至今我们还能信得过这些委员会吗?政府是否愿意让第三方的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去进一步深入调查,揪出那些犯罪者?显然一切将会是徒劳,因为犯罪者救在你眼前,然而你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如今泰益用公费造访牛津大学商学院进行演讲,不逊色于某人动用巨资在美国报章刊登“广告”,藉此来推广自己那套“伟大”的概念。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要谈“绿色发展”?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脸皮如此之厚者,明目张胆地扭曲是非,把自己的罪过当成功过来炫耀,在泰益家族的腐败专政之下哪会有什么绿色发展?这天大的笑话必须被捅破,好让国人、以至世人更了解泰益这人是何等之虚伪与狡猾。
仍记得臭名昭彰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召开巴格达新闻会谈时,被愤怒的伊拉克群众丢鞋子示威。伊朗保守派首相内贾德,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等分别造访美、英指名大学演讲时都受到了当地学生的“热情招待”。泰益这州政府独裁者要到牛津去宣布歪理,其名分虽然没有国家领导人般级别高、声名远扬,但相信Bruno Manser基金会等原住民人权组织、环保分子等相信会让他好看的。砂拉越就算还未有第二位的沙里夫玛沙荷或仁塔普等英雄出现,但一场争对泰益谎言的“飞鞋门”又未尝不可?
當今大馬 2010年7月26日 傍晚 7点26分
泰益独揽的土保党,美其名保护土著,实着在侵犯当地土著权利。砂拉越的许多树林被加以滥伐、天然资源被非法盗取,泰益家族、朋党乐于坐视不管,反正有的是从中捞取庞大的利润。无法无天之级已不在话下,泰益确实不输给早期统治砂拉越的“白种人王朝”,如今“白毛”集团掌控着砂拉越的实权,其剥削的力道相反更甚于那些殖民主义者的白种人;也因此,所有砂拉越的资源、产业等仿佛归他所管,你姑且可说泰益是砂拉越的“土著国王”,很明显原住民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还会失去更多的祖灵之地,任凭那些非法伐木者随意宰割。一些消息指出泰益家族在海外有很多资产,这有什么好出奇的?那些执政党的那些资深老大哥有哪些在海外听说没有房地产的?连前首相马哈迪在海外据说也有别墅,这确实不奇怪。在西马这里是一党独大(有待改变),而砂拉越则是泰益的家天下。莫怪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能运转那么多贪腐而来的资金,而陈水扁如今被法律所制裁,在牢里坐监了,而马来西亚的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客呢?谁来治理他们?
Bruno Manser基金会指出砂拉越的处女林如今仅剩下3%,相比较早前10%上下的数据少了一大撮,砂拉越森林几乎快要变成“botak”的状态了,然而这些不公谁来理会?原住民不懂得抗争吗?Bruno Manser基金会有许多主流媒体无法出示的证据,例如1993年本南族男孩被警察所行使的非法暴力杀害;2007年愤怒的本南族人得不到政府的回应,设下路障阻碍伐木工厂出入,而警察却开枪威慑示威者,把路障的树木锯断并焚毁。近几个月更是传出了伐木工人进入本南族部落为所欲为、禽兽不如的违反人道、践踏原住民之行径,而纳吉仅是装模作样登门拜访,设立了一个所谓委员会调查此事,问题是,至今我们还能信得过这些委员会吗?政府是否愿意让第三方的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去进一步深入调查,揪出那些犯罪者?显然一切将会是徒劳,因为犯罪者救在你眼前,然而你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如今泰益用公费造访牛津大学商学院进行演讲,不逊色于某人动用巨资在美国报章刊登“广告”,藉此来推广自己那套“伟大”的概念。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要谈“绿色发展”?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脸皮如此之厚者,明目张胆地扭曲是非,把自己的罪过当成功过来炫耀,在泰益家族的腐败专政之下哪会有什么绿色发展?这天大的笑话必须被捅破,好让国人、以至世人更了解泰益这人是何等之虚伪与狡猾。
仍记得臭名昭彰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召开巴格达新闻会谈时,被愤怒的伊拉克群众丢鞋子示威。伊朗保守派首相内贾德,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等分别造访美、英指名大学演讲时都受到了当地学生的“热情招待”。泰益这州政府独裁者要到牛津去宣布歪理,其名分虽然没有国家领导人般级别高、声名远扬,但相信Bruno Manser基金会等原住民人权组织、环保分子等相信会让他好看的。砂拉越就算还未有第二位的沙里夫玛沙荷或仁塔普等英雄出现,但一场争对泰益谎言的“飞鞋门”又未尝不可?
當今大馬 2010年7月26日 傍晚 7点26分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阿里的如意算盘
最近很喜欢关注依布拉欣阿里大叔,为什么呢?这人老爱出风头已不在话下,问题是,说话也拜托用点脑筋好吗?
说真的,这人确实没什么好关注的,特别是像土权组织这种老是挑逗种族议题的老少愤青集团。但308大选后的马来西亚可就不一样了,这位前巫统党员的土权老大,像青蛙那样一跳跳到回教党去参选,当选后又跳出去回到了老窝,继续当巫统背后的愤青老大(一个虚伪的“无党派”)。
大马政坛日夜吵吵闹闹、谁与争锋,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不放过谁,各自在不断争夺到底谁才是人民的至爱。在野党提出的民主与平等要尽快落实,但背后的问题接踵而来,而且就是那些不愿意分一杯羹的极右支持者,抓到了最好的时机,得以兴风作浪。
在野党虽然面临棘手的种族问题,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执政党国阵的矛盾;在面对着这些极端者时,仅有友党的马华等政党吭声,巫统整天装作爱理不理,大不了出面说几句不好这样就了事,根本就没想要解决事情。反正人家一党独大,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小问题,应该说,它们都是“同道中人”,不屑理会这种“芝麻绿豆”的事。也罢,反正我们也都知道巫统不好出面的事,土权组合几乎都做到最好了,不是吗?
阿里大叔在接受“the Nut graph”英文网络媒体采访的文章刊登时,许多人都大为不满,这厮算啥小?胆敢在自由的网络平台上唱他的种族主义大戏?其实也对,我们应当尊重他人言论,言论自由就是这么一回事。阿里大叔不就是在捍卫马来人的权益吗?
问题是,在时态逐渐在改变的情况下,在所有非马来人根本就没有危及马来人权益的情况下,大马需要走出一个封闭种族主义政治的情况下,阿里大叔这种极端的言论、行为算不算是种触意煽动种族情绪、任意胡作非为呢?
从那些威胁与羞辱其他尊群尊严的布条和游行示威,从土权不停在叫嚣分配不均匀、还需要求更多特权,特别是立法来限制其他族群(在此说明,不是非“土著”,而是非“马来人”)的权利等威慑性言论,谁会相信这是在用“和平”、“温和”的声调跟你说话?
而提出“一个大马”的那位却无动于衷。唉,也许想当年,他也是这样起家的,往事不堪回首呐!过去的事还是不方便提的好啊。
好吧,阿里大叔除了声大夹恶,往往也很天马行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仿佛自己是无敌的。什么叫巫统与回教当谈不来就解散掉?土权组织又来了,竟然在执政、在野两集团的两大政党面前挑拨离间、说三道四?再说,聂阿兹本来一直都反对什么两党和谈,谈不谈还需经过回教党内部协商后才得以决定;这种什么合并的阴谋诡计,唯有巫统想再度借用马来民族主义来拉拢回教党,使回教党里逐渐淡化掉的种族意识再度借尸还魂。
或许阿里大叔讲得没错,经过巫统许久的分而治之,我们早已分不清伊斯兰教与马来人的差异了,因为长期的种族主义教育已经把种族与宗教合二为一,藉此来巩固他们的权利不受动摇,特别规定王权、马来人特权、伊斯兰教是不可备受挑战的。所以呢,如今看到后果了吧?对于种族主义政党集团,这算不算是种自食其果呢?尝到了恶果,难道还有必要持续下去吗?
阿里大叔是个聪明人,他就会投机取巧,把那些陈规律令拿出来搬搬几下,又是一套好玩的东西了,结果土权组织反倒成了捍卫马来人的“先锋”,而其他人则成了老是只想剥削马来人的“臭虫”。继巫统之后,土权组织的极端种族主义将会是主流吗?
哀哉,马来西亚走到今天,真是大大不幸呐,节哀顺变吧!
当今大马 2010年7月24日 傍晚 6点41分
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
唐宝林:简论中国托派(《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其实,中国托派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深入研究中国托派,对中国托派作出正确评价,是党史、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诩,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抱住不放,推行一条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路线,结果到处碰壁,从失败走向失败。
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派大批党员和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派遣的学生纷纷回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留下来,参加了当时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发生于1923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开始是辩论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及一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到1926年,国际共运问题逐渐成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更成为争论的焦点。托洛茨基竭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而且“越到东方越反动”。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他抨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为此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多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他认为中国形势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共产党应该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都遭到否决。【注:参见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等文,载托著《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等,载《斯大林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立即抓住时机向斯大林发起猛攻,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进行辩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所有这些争论,在社会上,尤其在苏共党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也分成两派,分别追随斯太林和托洛茨基,从中央到基层,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上激烈地进行争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就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10周年纪念日时,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参加红场上游行队伍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殴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出国前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回国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多数又得以再次混进党内。如梁干乔到广东海陆丰在彭湃领导下搞过一段农民运动,区芳到香港太沽船厂搞工人运动,宋逢春到北方区委做宣传干事等。暗地里,他们则互相联络,筹组中国托派组织。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他们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组织成立后,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为此,1929年4月,他们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一个同名刊物(油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文件和讲话,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一批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接触到托派文件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问题的论述。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就曾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是光凭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完全倒向托派。他们转向托派的关键,是接受了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背景。
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大会前夕,已经被放逐到苏联东南边疆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长文,猛烈批判国际纲领草案,全面攻击了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他要求这篇文章在国际六大上散发,让各国代表公开讨论。共产国际只翻译了一、三两部分,发给少数几个党的代表团阅读,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不料托洛茨基的文章在相当一部分代表团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不顾禁令,把文章带回国去,也成立反对派,于是形成继第二国际分裂之后又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192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又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此文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接着应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革命没有到来前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只能进行议会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经过长期合法、非法、不流血(非战争)的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最后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六大规定的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攻击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中国托派这种理论错误的根源,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正如毛泽东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上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53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中国托派一直没有共产党人这样的认识,而坚持托洛茨基为他们规定的城市中心、议会斗争的道路。
陈独秀等人接受托派主张后,就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8月5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他们则自认有国际背景,有恃无恐,坚持错误立场,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你们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行使威吓手段的、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注: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
党中央通过作决议、个别谈话、开会辩论、多次警告等各种方式,千方首计地教育挽救他们,他们却毫无认识,拒绝悬崖勒马。就这样,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在开除前,他们就曾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与归国留学生的托派小组织谈判,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因对方条件太高未遂,于是他们就单独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示不承认被开除,仍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并成立了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他们创办了《无产者》作为机关报。陈独秀在创刊号及第2期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以教条主义的口吻,攻击中共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谩骂红军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
这两篇文章是托陈取消派(也是整个中国托派)反对我党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代表作。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注: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陈独秀和托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已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本质的不同: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教育改造下,广大贫苦农民将克服自身的弱点,发挥革命主力军的强大威力,去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只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农民意识化”的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另外两个托派小组织: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和以赵济为首的“战斗社”。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催促下,4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几个决议,选举了9人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组成常委会。
4个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互相之间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陈独秀对中国托派组织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找本派及其他各派的头头做工作,在说明中国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特别强调要乘当时中共党内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乱,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为此,他甚至说:“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若还不迅速统一起来,这简直是“罪恶”【注: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
中国托派组织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不断受到破坏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原托陈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其家属10数人被捕,5个常委被捕去4个,唯陈独秀幸免。家属关押1月后释放,其他人分别被判处15年、10年、5年及2年半徒刑,托派中央顿时瘫痪。不久,陈独秀吸收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8月又被捕去3人。
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蒋介右一度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陈独秀以托派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热情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和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上海抗战、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除了主编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外,他还最后一次自编《热潮》周刊,推动民众运动,企图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领导机关处于大破坏后的瘫痪状态,再加上中国托派内部又有一帮人视“反日”、“爱国”、“救国”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涨和衰退,陈独秀只得“望洋兴叹”。他曾写信呼吁与中共中央共同领导民众运动,也遭到拒绝;他提出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以“首先推翻革命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注:《统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校内生活》第3期。】的主张,也无人响应,甚至遭到托派内极左派的严厉批判。
1932年春,陈独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5人常委会,并准备在华北和上海工人中重点开展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但是,当托洛茨基从陈独秀的来信中得到这个消息,并指示他们如何提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注:托洛茨基:《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07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的口号进行斗争时,他们的新班子却在10月15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这次是全体常委(包括陈独秀)、机关报及联络站等被一网打尽。国民党政府最后以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为由,判决陈独秀等人“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注:《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1933年5月24日。】,各处有期徒刑8年、5年、3年等。
陈独秀等被捕后,中国托派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委书记会商曾拼凑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不到一年倒台三次。1933年12月才成立起由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等3人组成的比较稳定的“临委”。由于陈独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间,他的一些主张一直遭到中国托派内部甚至托派中央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临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内部讨论上,以求托派内部思想和步伐统一后,再开展政治活动。讨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一年多,狱中的中国托派分子也参加了【注:狱中托派通过经常去探监的联络员刘静贞(郑超麟妻子)建立了与上海临委的联系。】。讨论集印了三大本,每人都以“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北平来的史朝生、刘家良等几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来华的特派员、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借充实“临委”机会,在1935年1月13日召开“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除了陈独秀、陈其昌和尹宽等人。他们批判陈独秀提出的托派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以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曾在1933年发表宣言,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反战会议,并在福建事变中,派代表与第三党拉关系。新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都违背了托洛茨基规定的托派不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原则。
上海代表大会还把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准备建立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3个月后,1935年4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成立中国托派政党的努力,遂成一枕黄粱。
1935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宣言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等,百般挑剔,竭尽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胡说“‘红军’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党(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注:政治决议案:《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1937年2月21日通过),载《斗争报》第3卷第2期。】等等。
中国托派推行的这条反动路线,使他们在抗战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
抗战中为侵略者张目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汉活动,企图以抗日和民主为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但是,自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切。所以,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1942年5月27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
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人民’、‘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种阶级。接着,他们断言:“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最具有欺骗性的是,他们还用种种漂亮的油彩把这种无比丑恶的理论涂抹起来,蛊惑群众,宣称:“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注: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均载《火花》第3卷第5期。意因是郑超麟的笔名。】
把极左和极右如此丑恶地结合起来,恐怕在中外机会主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样的托派分子,如果当时钻进抗日阵营,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而决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革命”。
中国托派的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客观上起着破坏抗战、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
中国托派这种表现,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严正的批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托派本身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大搞逼供信,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所谓托洛茨基1935年12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注:据1988年8月4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30年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四大错案平反,指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4年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王明、康生在工作中又夹杂私人恩怨和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野心,于是,中国抗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发生了3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这就是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1939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300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和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更不是汉好。
1941年7月13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操纵下,中国托派召开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在对国民党、尤其是共产党进行了一番例行的攻击后,声称中国4年来抗战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他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注:《斗争报》第5卷第5期。】。大会选举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向敌我矛盾转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走上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阶段。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
开始,蒋介石以和平谈判为烟幕,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时,中国托派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不要诉苦,不要控诉哪一方先调兵,先遣将”,以及“何方先进兵,何方先发第一炮”,国共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注:凤冈:《内战、革命与共产党》,《新旗》第17期。】。“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的决议》,号召解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中国托派这里指的“错误与叛卖”,是指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搞“阶级调和”,“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叛卖工农”等等,并且胡说:共产党这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资产阶级当苦力”【注:舒严:《中共军事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新旗》第19期。】
1948年春,当全国人民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根据是,共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注:《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编者答读者周永新的信),《新声》第2卷第2期。】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就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甚至建立武装,企图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军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注:《内战问题的总结》,《叛逆者》第1期,1949年11月15日。该刊是“多数派”潜伏组织编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当时中国托派两派加起来,总人数也不超过500人(“多数派”300多人,“少数派”约100人),要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只能是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他们称共产党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注:阿陈:《如此制止世界大战》,《新方向》第3期。】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中国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百般诬蔑、抵制和破坏。他们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个别人甚至与美蒋特务及土匪勾结,搞武装暴动等。
这样,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共产党、与人民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敌我矛盾。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政权,决不允许颠覆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解放以后中国托派的活动完全属于颠覆活动,超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的范围。这样的组织,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取缔的。但是,基于抗战初期反托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中共中央对解放以后的肃托斗争,处理得比较慎重。在建国初期的几大运动中,都未触动它,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中国托派在大陆上的全部组织和活动。托派当时对中共掌握政权后未像苏联那样立即大规模镇压他们曾感到奇怪。王文元在回忆录中说:“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人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不曾清楚。”【注:《双山回忆录》第287、288页。】于是,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共软弱可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活动越来越猖獗。
终于,他们的末日来到了。1952年12月22日,中国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中国托派组织。
可见,中国托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说它是“反革命集团”,是指解放以后;解放以前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虽然它在理论上的错误,有时比“反革命”、“汉奸”还严重。同时还应指出:人民政府对在取缔中国托派组织时逮捕的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而是着眼于教育和改造,并对他们获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如郑超麟、濮清泉、赵济、蒋振东、喻守一等这些“中央委员”一级的托派分子,都安排在省、市或区一级政协工作。对香港及海外的中国托派分子,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在对他们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也并未放弃争取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自信的表现。而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托派,早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只能充当反面的历史见证人,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陈恩来,敢说就敢当,有风度点啦!道歉吧!!

民政党吉打组织秘书陈恩来的“老而不死便是贼”出自何典?可见此人是肚里有墨水之人,这句话原本写作“老而不死是为贼”,我们不妨看看其出处:
此话乃出自《论语·宪问》(14.43)中的一句话:“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它可以被解释为:责骂老而无德行者的话。元朝的某无名氏在《盆儿鬼》第三折也记载了这番话:“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正是你这样人!”(摘自百度百科)
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陈恩来quote得不恰当,前提是所指者必须是“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讲得俗气点,这句话是骂某人少时没礼貌,老了便是混帐之义,是问陈恩来指的顽固之人,是何来的“老而不死便是贼”呢!?
很明显这就是面向老者的骂言,借问陈恩来你不是骂老人请问是在骂谁呢?你在言论广场所受的委屈大家都能理解,问题是那就是言论广场,好或坏你讲你的,人家骂什么干你屁事?槟城有最糟糕的言论广场?难道那些刻意被屏蔽掉的、或者只被允许有一家之言、一党独揽的广场才叫做最好的言论广场?在没有观众能发表心理不满,鸦雀无声仅能乖乖听你讲的场所,也许就是你所谓的“最好的言论广场”吧?
你管民主行动党的议员或首长有多Pariah有多不入格,你做好自己便得了不是吗?在场的老人不是老人,更是老百姓,你如此没有风度,跟老百姓闹不去还想在政坛上混啊?有没有想过老人为什么不满?你可不要告诉我说是某某人派人来搅局什么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前朝的政府办事不力,没有为他们生计着想不是吗?
可陈恩来干了什么呢?来到人家的场呛声、骂别的政党就很客气了,却还不甘人家对你来呛声?这算什么态度?槟城好不好管你什么事?槟城老人表达不满难道就证实人家是野蛮、无理的人吗?你有胆量说出这番言论,就要有胆量去承认错误不是吗?槟城有什么何止得罪了槟城人,就连“老而不死便是贼”这句话你就算说错也得道歉,为何?谁叫你说错话引错词?你骂的虽是刻板固执的人,但那句话确实针对老者的,真还算是个误会吗?
何以见得槟城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只有你讲就算了。你可以表现得很“儒家”,但普通百姓可没有这种忍耐力,不爽就骂你很自然。你可以不爽槟城政府、不爽老人、甚至不爽这种民主、这种言论自由,那拜托你去学习学习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演讲角,看人家是怎么在那儿分享个人主张、争辩课题吧。要像你这样的性格,那言论广场岂不老早就失去了榜样?
别用你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他人的错误,你自己的错误又审视了没有呢?身为个政党的人物,连肚量都没有,还想出来“捞”?有风度点,正视自己的错误吧,胆敢去道个歉赔不是吧。想跟老百姓过不去,岂不害了你自己,更害了你的政党的名誉?到时请不要又怪槟城、怪政府或是怪老人了,就怪你自己衰多嘴、没气度吧。得罪了百姓,你就真失格了。
当今大马 2010年7月21日 晚上 10点57分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民联的《民联报》与人民的期望

《民联报》是个不错的概念,它应当早日出版。民联结盟已有两年之久,在意见与意识形态方面等问题却一直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各党派之间的矛盾确实不少。我们都知道民联的初始概念在08年大选前的互助精神早已体现出来,选后更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在野党的三大势力姑且抛弃以前的恩怨,拉起手来合作,促成了人民联盟的建立。但相比其国阵的种族政党集团,在野党集团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是一个新的在野党联盟,跟专断了执政权五十几年的老集团决斗,怎样也要有个共识。
三个在野党里,当属回教党的意识形态最深厚,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回教党的创始本是为伊斯兰教的马来民族争取权力的,早期是个格外极端、结合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政党。近几年来,为了抵抗国阵-巫统的贪污腐败与种族主义,回教党也逐渐理智,如今它采取的是温和路线,并且鼓励种族和谐,主张不分你我的平等政策。人民公正党的前身国民公正党也是个从巫统分离出来的马来民族政党,自从与人民党某派融合,更深知了种族主义的弊病,选择将仅限马来人的标志去除。民主行动党更不用说了,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最典型的标语,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标的火箭提倡的是民主、平等。
虽说后二者看起来并无什么确切的意识形态,唯独回教党,人们怀疑并非世俗政党的它能否值得被信任,对非伊斯兰教徒来说始终是个问号。莫怪民族政党里的马华公会老是职责民行党与回教党巴结搞“回教国”,巫统却在另一边威慑马来人要小心华人挑战马来特权等,这种“两面蛇”的猴戏我们难道还不清楚吗?避免受到敌人的恶意所影响是最重要的,近几年来巫统老是提出与回教党联合,企图把它从民联分裂出去。这些“反间计”还有例如跳槽事件,人民公正党党员的不稳定较高,一直传出有党员集体退党;霹雳州政府事件已经证实了这点,那些脱党的“无党派”便是其中的例子,他们现在自称是“中立”;还有为了自身利益入党者,例如土权组织老大阿里借回教党名誉当选等事,还有几个月前退党的民行党州议员等便是如此。
三党如何团结在一块?这是件棘手的问题,一份报纸能够做些什么呢?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建议是由回教当副主席所提出,明显可看出回教党的意志比谁都坚定。近来政府刁难各在野党党报的行为是有目共睹的,民联三党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跟政府与执政党对干。对干的主要手段是透过与执政党媒体不同的媒体,这点相信也不是什么新鲜课题,08年大选在野党之所以逆转大胜,靠的是与主流媒体全然不同的反对声音,还有借助网络的力量等。但局限在于政府对印刷媒体的监控程度极高,譬如他们有权不更新准证或查禁报社;网络媒体在乡镇地区亦并不流通,看看大选的成绩便能知道,乡镇地区的选票仍是国阵稳定的票仓。要打通民智,就要散播真相,《民联报》尤其可行性,不但可以传达主流媒体所刻意隐瞒的新闻报道,也可间接宣传民联的政治主张,要做到这点民联必须紧密联系、多集合起来商讨事宜、促进彼此间的关系、化解意识形态的矛盾,来激励人民的思考,鼓起他们的勇气与判断思维。
要抗衡国阵-巫统的民族主义的陈腐思想,民联必须独创出一个多元的平等理念,时刻紧贴在一起,化纷争为力量,摒除掉矛盾的、固执的一党之见,寻求各成员党的共识,来抨击种族主义政党的虚伪与其日渐形成的危害性。民联不能只是德国的基民党-基社党联盟,又或者是英国的保守-自民联盟,毕竟他们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更是政党后为了巩固执政权而结盟的。马来西亚的主流思想一向是国阵的后殖民主义方针-分而治之,民联的目的是实现多元、民主、平等,在这么一个民主不成熟的国度、在这么一个种族因素的复杂的国家、在三党之间仍存有歧见的联盟该如何实现其愿望?人民在等待着,因为抱有希望的大部分理智的人民更愿意看到一个不同于当今腐败、极端、分裂、离心等严重病态的新马来西亚。
期待有一份人民联盟的报纸,来打开大马民主的第一道窗口。

当今大马 2010年7月20日 中午 12点32分
“不代表本党立场?”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对于马华公会来说可能十分管用。林祥材的“华权主义”,该党说是胡说八道、一家之言、表达错误等等,不但被人攻击为不理智行为,甚至还被慕尤丁与土权组织等认为还不错,是是非非,一时让人摸不着头脑。
“华权”还未顺利告一段落,议论纷纷,无聊透顶之时,轮到了网民的“靓照”粉墨登场,这次的主人公的视角换成了马华公会巴生区主席郑敬保是也!郑敬保的影子穿梭照片的各个角落,十分显眼,网民打出的有趣标题则是“马华已经成为土权成员”。在我看来,这有点夸大了,不妨看看那些照片,里面不仅有马来人,还有印裔,更不要说有郑敬保等华裔的影子,这是国阵阵营的示威游行,马华公会在里头非但不是“奇景”,应当说是“应该的”才对。
由于土权最近老是行风作浪,搞得巫统老大跟马华之间十分尴尬,马华公会否决自己不是“乘客”不是小弟,却拿巫统大哥没办法。土权组织这巫统的老表能奈马华怎样?马华不是已经成为土权的成员,而是成为了进退两难的代表,左右为难,很难做人呐!身为民族政党,一边又要应付老大的压力,另一边又要反对老表施压,却不知老大跟老表其实形同一人,只是各自有所发展而已。也因此,郑敬保这名马华的区主席在巫统与土权支持者居多的场子上,怎样也要给面子的不是吗?所以才造就了这么个有趣的“和谐”场景。
问题是偷砂问题本身就源自前朝的当权者基尔,现在雪州民联政府却被他反咬一口成为偷砂的罪魁祸首,基尔的贪污腐败、饱吞私囊的丑闻早已家喻户晓,但谁能制裁他呢?民联政府要挖他底逮捕他都很吃力,更何况他的后山那么硬,更重要的是后面还有一班是非不明的巫统与土权组织等忠实支持者。而感谢网友所提供的照片,我们得知马华公会也有份参与“挺基尔”的阵线里头去了,郑敬保就是代表之一。
问题不在于这是否跟土权组织有无干系,又或者是不是国阵支持者的游行示威(其实怎么看都好像是巫统的独角戏而已),而是郑敬保你到底有没搞清楚状况?基尔等前朝鼎鼎大名的贪官污吏还有劳你马华公会去为他抬杠?为他示威游行?当然,没人反对示威游行表达个人意见,但也摆脱你搞清楚状况再加入吧?而非毫无理智地、盲目地去“顶”所谓国阵阵营邀请参加的集会,这样一来马华公会不粘上污点才怪呢。郑敬保又在场巧遇土权组织,更衰!真不知他脑里在想些什么。说不定在利益分摊上有鬼?谁知道?鬼才知道!
我不确定马华公会在这场游行集会是否被郑敬保“代表”了,但因为这起有趣的事件,马华的脸又不知要摆哪里去了。不过,马华也可以出来澄清:“郑敬保当天的行动,不代表本党立场,谢谢”。
(这篇独家!!当今大马没刊登出来!)
2010年7月18日星期日
新闻被蹂躏得很虚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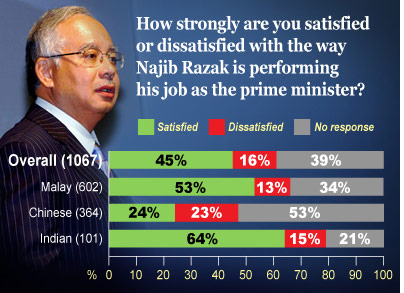
何以见得?其一,玩文字游戏是也。为什么涨价不能说成“涨价”,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不是涨价又是什么 呢?难道得“九唔搭八”变成“减”价吗?什么“价格调整”等“杀伤力较弱的字眼”?刻意模糊人民的视线,故意让人民摸不着,仿佛知情权被剥掉一层似的。知 道了“价格调整”难道就会心安,并且不会再计较须为日常用品支付更多费用了吗?
仍记得2008年时安华与沙比里 针对石油涨价的辩舌战,阿都拉执政时期什么都涨人民早已有目共睹,现在换了个新首相纳吉,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在继续涨。而涨了还好,这又跟媒体有何干 系?为什么要对“涨价”一词如此敏感?涨价就涨价,汇报不就得了吗?然而当各大报章遮遮掩掩似的在头版上打出暧昧的表达方式之时,我想纳吉先生应该会挺高兴的吧?其权威自然是无法被挑战的。
先不要说啥危言耸听、扰乱民情等较为激烈的情绪,又或者是被在野党抓住矛 头,得以从物价上涨方面攻击政府。关键在于,政府凭什么可以控制报纸的报道?他们又不是党报,起码报道语言也不会极端到哪里去不是吗?哪会有什么民愤、什 么民怨?我敢说,物价上涨本来就会惹民愤、犯民怨,在文字上动手脚究竟有何意义?
什么“新价”、“调整”、“最 低”、“轻微”全属扯淡!再看看这些看出微妙头版字眼的报纸,绝大部分是有“国营”背景的,其附庸的态度确实是百分百遵从,毫无自己的主见或不满。这次不 得不赞扬《中国报》的做法,中文报一直被极端分子抨击为“极端”,其实它们有很多确实是挺乖的,也许《中国报》不听话?敢敢刊出“涨价”两个字来挑逗政府 的神经。涨就涨,实话实说,新闻就是为了报导事实,否则就是欺瞒。换成“调整”有欺诈的嫌疑,因为新闻被做了“修正”!
至于其二,“反虚假新闻小组”是也。说是为了回应《哈拉卡》的要求,这可是政府难得愿意听取在野党一方的意见啊,不是么?但话说实在是美其 名,实则是要严加管制媒体。从《公正之声》一路闹到《土权之声》,再一路牵连到《哈拉卡》、《火箭报》,能禁止的都禁止,能吊销执照的都吊销,搞不好还得背上没证据胡乱说话而抓去坐监的风险。
问题是,一直不停在鼓励并提倡分而治之、种族仇恨的到底是谁?谁该为这些 后果而负责?是谁在分裂一个马来西亚?我想人民的心里是最清楚的,无非是那些极端种族主义者,什么青、什么权之类的东西,与新闻有何干系?明显的这几次的 党报风波事件的燃起,发起事端的那方必须负责,但借机大做文章、煽风点火者也有罪!
现在好了,要反虚假新闻,听起来绝对是正义的。然而这种东西在政府的权柄之下,也许是个模凌两可的概念。譬如你某某立场不同的媒体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就可以以莫须有来定你散播谣言之 罪。而立场完全倒向他们的那一方的媒体,老是挑起不必要的极端言论,却可以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最虚假的,莫过于把自己人所做过的事儿当没一回事,却 对反对声严加打压的可耻行为。要真的有心想搞,我想人民将得到的结果是:一、耳根清静,那些那些发布不实报导者都会被严打、取缔;二、仅有一家之言,没有 异议的声音可听可阅,因为“虚假新闻”都已被消灭,我们只要听“真实”的、“和谐”的新闻就行了;三、假象,把自己包装成最“真实”的新闻,其实问题根本 没有解决;他们继续喊,而你只能装作没知觉。假亦真时真亦假,不要“反虚假新闻小组”,应当组织“反虚伪新闻小组”才合理吧?
当今大马 2010年7月18日 上午 10点19分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误入阿里大哥的圈套!

易卜拉欣.阿里的为人着实野蛮,我想认同这点的人铁定很多。对于华权方面的问题,林祥材承认自己说错话,马华公会认为是林一己之言,不代表“本党立场”。接着看看巫统大哥有何反应,有趣的一点在于“少壮派”纳兹里变得很开明,简直跟从前的极端态度判若两人,他反对种族搞任何的权,这等于是在分裂族群团结;而相反的“保守派”慕尤丁却觉得无所谓,他搞他的土权,你也搞你的华权,只要不违法,随便你们怎么搞。千奇百怪,各言其说,到底谁对谁错?既然祸水是源自于易卜拉欣.阿里,那应该就得看这名罪魁祸首怎么说。
怎知死不悔改,明明自己捅了蜜蜂窝,闹得满城的种族特权风雨,硬说是执政党与在野党是在害怕土权组织,还自比多伟大,真是不要脸!问题是,谁不害怕土权组织?巫统老大哥都不敢声称自己很极端,时而为自己很“中庸”而感到骄傲,然而却有这么一个老是在煽动自己被剥夺、马来特权不允许侵犯的NGO在那里叫嚣特权,这还算不算极端?
然而不认错倒无所谓,知道自己极端就好,却又把其他种族的NGO也拖下水,把华总、董教总、Hindraf等都打成了跟他们一样的“同类”,仿佛马来西亚一夜之间多出了很多极右组织,好像很多团体一直都是跟他们平起平坐似的。问题是,华总、董教总维护了华社、华教利益那么多年,靠的是政府吗?他们几时有说过跟土权组织同腔同调的极端言论,大搞所谓的“华权”?而Hindraf最初是维护一群贫困印裔的组织,而请问维护他们族群的基本权益是“印权”吗?他们极端?我敢说要不是镇暴队要不是毫无理由驱散群众,那场和平示威会变成骚动吗?还有那些少数的原住民“土著”又该如何处置?土权到底维护的又是谁的利益?有天伊班人甚至色奈人也出来搞抗议,他们搞的是“土权”吗?
明显的,搞什么权都不是,土权组织完全是以易卜拉欣.阿里为主的政治把戏,他的那些极端话语,一边威胁着自己的族群,另一边则威慑着其他族群,他当然希望土权搞得越来越好,什么五万人、二十万人,好让他为自己贴金,好把自己当成“现代汉都亚”不是吗?不过,我们会因此而惧怕吗?当然不会。一个NGO要是真盖过了巫统的头,他们真会就这样坐着不管吗?最使人汗颜的还是慕尤丁,非政府组织是以人道主义、助人为本当出发点的,怎么弄得他们好像都在搞种族主义似的?这点嘛,真多亏土权组织把NGO的美名“搞臭”了。(哦,他声称自己是所谓中立的无党派国会议员,但别忘了他可是在回教党的帮助之下当选的,他可是一名优秀的跳槽者。)
由于土权组织的小动作,我们“一个大马”政府的部长都闹得团团转,胡乱讲什么权、搞什么权,岂不是等同于扰乱种族和谐吗?请土权组织认清事实,非土著从来就没有挑战宪法第百五十三条,而且我们也不会那么做;而新经济政策的截止日期是一九九一年这是谁都知道的,可后来却又被前首相马哈迪无限延长了。宪法规定的建国纲领,但扶贫政策却并非永久的保障不是吗?非土著哪有触犯土著特权?无可怀疑,我们都误入了易卜拉欣.阿里所设下的圈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管是国阵还是民联都得提防小人呐,别小看这个堂堂NGO主席,他可是专搞极端、出言不逊、刚愎自用、且善于推卸责任的阿里大哥啊。
当今大马 7月14日 晚上 10点05分

Greedy your mother!And we pay cukai to feed your fucking asshole?

Ibrahim Ali,a fat fucking hardcore racist!Fuck You,Retard!!
本人的微型小说集子《短距离》,欢迎各位支持下~~^^

新加坡盛大小说阅读网-《短距离》页面:http://zb.sdl.sg/zh/b/8000014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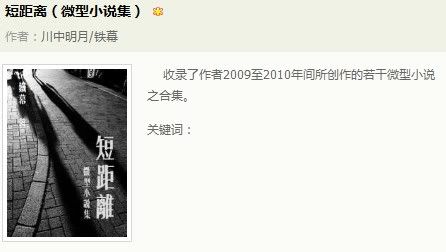
2008年跋山涉水、离乡背井到相当郁闷的中国大陆深造,副学士毕业后趁着半年的空隙一度努力写时评,随后因与大马产生了疏远的距离感,以及课业繁重而中断掉。经常做的事情便是空闲时写诗,偶尔竟也开始写起了好久没碰的小说。当然,或许是自己太过急性子,凡创作过的长篇都半途而废,所以我选择书写比短篇还短的微型小说,直接了当,而且每次都能写好多不同的故事。从2009年中期开始写下第一篇,累计下来已有大约二十几篇,近几个月由于赶论文及答辩而停止了。姑且暂时先停下脚步构思,把先前所写过的拙作拿出来发表一下。~感谢现今网络的便捷,制作一本书不用刻意印出实体来(当然,印出来捧在手心细嚼一番最好了~),可以直接放在网上让人们阅读,不另收费。告别了中文系,并不意味着我告别了文艺写作,长路漫漫,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笔杆子无敌!
“你不想写你最想写的小说。”-Philip Larkin(1922-1985)
2010年7月14日 陈勇健 南京市
标签:
分享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不要华权,更不要土权

马华公会近来所发表的“正义言论”不断,不仅挑逗了国阵内部的神经,更是直接敲响了“一个大马”的警钟,这些确实是可圈可点的。问题在于,马华身为一个华人政党,在巫统这么一个偏右的、时好时坏的老大哥之下,到底能怎样维护华人的权益问题?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却弄得左右到处碰壁,一脚踏入陷阱里。
马华副总会长林祥才的“华权”对于华人来说听起来固然好,但岂不又重复了极右的土权组织的老调?学起极端分子的诸如“肥水不流外人田”、“楚河汉界”的幼稚圈套里了?
要是真的有心建立一个多元民族共生共存,团结平等的马来西亚,那些偏激的东西都必须受到严格禁止。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在抵制民主,问题是,我们又何必再为自己到底是不是“寄居蟹”而困惑?而另一方则一直在老调重谈,如今“寄居蟹”的当事人却还得以卷土重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那些人老是用煽动性的种族主义言论来攻击其它族群、一直在那儿说华人、印度人等是外来人,不喜欢就滚回去之时,我们难道就得选择硬碰硬?这是个错误的概念,两种极端要是硬碰,必然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冲突。
马华公会要是真有心,就不要跟拷贝那些极右流氓的调调,胆敢去质问巫统为主导的国阵到底有无心搞真正的“一个大马”岂不是更加?“一个大马”若真是两头蛇,继续搞分而治之,持续种种的煽动关于马来主权的争论性课题,那它必然是个失败的口号,新经济政策更不用说是个失败的政策。
我们应当了解到,大马所遭遇的不平等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种族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特别是以巫统所领导的贪污腐败的政府,试问到底有多少利益是真正平分给所有人民的?我们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种族课题越烧越严重,还不都是精英阶层欲抓住权力不放,一直妖惑着普通的百姓,将煽动性的种族议题反复炒作,难道不是吗?土权组织为何如此之嚣张?还不都是老大哥在背后纵容它放火?
我个人认为林祥材的话并非错误传达,若这真是肺腑之言,无可否认他说的话不算极端,而是针对近来不停升温的,尤其是极端分子所煽动的种族矛盾的回答,只不过这种“以毒攻毒”的招数不仅无效,反而还会让那些极端分子有机可乘,借机会来攻击华社挑战马来主权,这不就祸害了华人吗?我想林祥材不是口出妄言,只是心急口快而已吧?
建国以来,华社在压力的逼迫之下学习自力更生、自我保护,一贯秉持着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传统价值观。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获得公平对待,基本权益受到保障,不要再听到啥“寄居蟹”、“滚回中国去”等的歧视性言论,做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公民而已。将种族问题政治化是极端分子善用的手段,因为他们未曾从民生上来看问题,仅吹捧自己的固执己见来煽动他人的神经,以便制造祸端。
马华公会历来都充当着国阵内谏官的角色,如今看来似乎已逼到窘境,无路可走了。然而,巫统老大哥却还在顽固进行他那分裂族群的意识形态;身为老小的国大党更是一直在谈自己代表印裔的问题,却不去想想该党主席为何被自己族群淘汰掉。回过头来想一想,种族政党依然是大马唯一的出路吗?分而治之亦然?马来主权亦然?这些被搁在一旁许久,长满了蜘蛛网的棘手问题,巫统要是不出面解决掉,国阵里的小弟们不动则不伤、动则荆天棘地,那还谈什么“一个大马”?在我们的眼里,大马貌似有好多分散个体!
当今大马 7月12日 晚上 10点08分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向《公正报》学习
一党之喉舌,虽不能代表所有人(我国不是专制国家),但对于想了解甚至支持它的人,党报确实有其价值所在。在大马,在野党党报在能尽可不招惹到内政部刁难的情况下,仅能在党内私自发售,例如行动党的《火箭报》必须私下订阅,在任何报摊上都看不到。唯独《哈拉卡》与《公正之声》等二报能大剌剌摊在市井,到处发售,这何尝不是件好事?我们有阅读任何报刊的自由。
但近来针对所谓的敏感话题上,内政部开始“动真格”要取缔《哈拉卡》、《公正之声》二报,使人不禁怀疑“一个大马”到底是走向更为宽容,还是企图消灭异己,搞仅受政府严厉看管的新闻独裁?
 看了昨天《当今大马》的新闻,得知《公正之声》出怪招,反正你内政部那么暧昧,要查禁吊销与否迟迟不肯给予答复,而它最终还是一份周报(weekly),每星期固定要印刷发行一份的。由此可见内政部分明是想拖延时间不让你出版。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绝妙地将报名转换成了《公正报》,这次“suara”字眼真的不见了,不见“喉舌”(土权组织的喉舌话说也是suara不是吗?),仅见“公正”!
看了昨天《当今大马》的新闻,得知《公正之声》出怪招,反正你内政部那么暧昧,要查禁吊销与否迟迟不肯给予答复,而它最终还是一份周报(weekly),每星期固定要印刷发行一份的。由此可见内政部分明是想拖延时间不让你出版。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绝妙地将报名转换成了《公正报》,这次“suara”字眼真的不见了,不见“喉舌”(土权组织的喉舌话说也是suara不是吗?),仅见“公正”!
新出版的党报还标上了“只供党员”和“无序号出版”等,完全回归了党的立场上发行报纸,挑战权威不得将党报售与非党员等毫无理由的教条式律令;而且该报也转向了内部的公青团出版,而非交由其它出版社等之做法,完全是为了对抗内政部不更新准证的“《公正之声》”。人民公正党摆明就跟内政部干到底,你查封的是《公正之声》,可我出版的是《公正报》;你说不得发售给非党员,但我早已写明了此报“只供党员”,不但没有违法,也不必为买者是否党员负责;你不给准证,我就“无序号出版”,作为一份党喉舌继续留存下去,问你死未?如此婉转的手法,还真是让人感到出奇,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想法!
《公正之声》虽是党喉舌,但它乐于报导一些主流报章上见不到的“极度”负面消息,口碑极佳。当然,所谓的党喉舌(不管执政党抑或在野党),你亦可认为这是该党的一家之言或者造谣撞骗,又或者是为了攻击其他党派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报纸。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份党报,内政部可以不发给新准证,它依然有权可以继续发行,它就由外部转向部内,在内部跟你“打游击”,除非政府真的采取行动,威吓非党员不得买其报纸,否则它将尽可能传递到那些愿意阅读此报的人手中。
反正解释再多也没用,人家就是故意针对你来打压!还能解释什么?回教党喉舌《哈拉卡》报不妨也效仿《公正报》的做法,“未能准时向该部门呈交每期的刊物副本”分明是强制监督,与“向非党员出售刊物、将刊物放在未被指定的地点贩售”等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难道不是吗?只要是党报,我就没理由听从你的指使。
《当今大马》 7月12日 早上 8点54分
但近来针对所谓的敏感话题上,内政部开始“动真格”要取缔《哈拉卡》、《公正之声》二报,使人不禁怀疑“一个大马”到底是走向更为宽容,还是企图消灭异己,搞仅受政府严厉看管的新闻独裁?
 看了昨天《当今大马》的新闻,得知《公正之声》出怪招,反正你内政部那么暧昧,要查禁吊销与否迟迟不肯给予答复,而它最终还是一份周报(weekly),每星期固定要印刷发行一份的。由此可见内政部分明是想拖延时间不让你出版。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绝妙地将报名转换成了《公正报》,这次“suara”字眼真的不见了,不见“喉舌”(土权组织的喉舌话说也是suara不是吗?),仅见“公正”!
看了昨天《当今大马》的新闻,得知《公正之声》出怪招,反正你内政部那么暧昧,要查禁吊销与否迟迟不肯给予答复,而它最终还是一份周报(weekly),每星期固定要印刷发行一份的。由此可见内政部分明是想拖延时间不让你出版。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绝妙地将报名转换成了《公正报》,这次“suara”字眼真的不见了,不见“喉舌”(土权组织的喉舌话说也是suara不是吗?),仅见“公正”!新出版的党报还标上了“只供党员”和“无序号出版”等,完全回归了党的立场上发行报纸,挑战权威不得将党报售与非党员等毫无理由的教条式律令;而且该报也转向了内部的公青团出版,而非交由其它出版社等之做法,完全是为了对抗内政部不更新准证的“《公正之声》”。人民公正党摆明就跟内政部干到底,你查封的是《公正之声》,可我出版的是《公正报》;你说不得发售给非党员,但我早已写明了此报“只供党员”,不但没有违法,也不必为买者是否党员负责;你不给准证,我就“无序号出版”,作为一份党喉舌继续留存下去,问你死未?如此婉转的手法,还真是让人感到出奇,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想法!
《公正之声》虽是党喉舌,但它乐于报导一些主流报章上见不到的“极度”负面消息,口碑极佳。当然,所谓的党喉舌(不管执政党抑或在野党),你亦可认为这是该党的一家之言或者造谣撞骗,又或者是为了攻击其他党派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报纸。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份党报,内政部可以不发给新准证,它依然有权可以继续发行,它就由外部转向部内,在内部跟你“打游击”,除非政府真的采取行动,威吓非党员不得买其报纸,否则它将尽可能传递到那些愿意阅读此报的人手中。
反正解释再多也没用,人家就是故意针对你来打压!还能解释什么?回教党喉舌《哈拉卡》报不妨也效仿《公正报》的做法,“未能准时向该部门呈交每期的刊物副本”分明是强制监督,与“向非党员出售刊物、将刊物放在未被指定的地点贩售”等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难道不是吗?只要是党报,我就没理由听从你的指使。
《当今大马》 7月12日 早上 8点54分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极端,极端,极极端!
 在大马政府在大肆鼓吹和谐之时,有什么能比《土权之声》的出版更极端的事儿呢?这份仿佛就像是《公正之声》的copy cat版(因为二者都是suara),指责《公正之声》诽谤并支持其遭到吊销执照,而紧接着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虽说非党派性质,但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极端?
在大马政府在大肆鼓吹和谐之时,有什么能比《土权之声》的出版更极端的事儿呢?这份仿佛就像是《公正之声》的copy cat版(因为二者都是suara),指责《公正之声》诽谤并支持其遭到吊销执照,而紧接着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虽说非党派性质,但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极端?土著权威组织是什么东西?要是你说巫统是“温和”的种族主义,那么该组织就是“极右”的种族主义,老是在那里争辩土著权益的不满足,鼓吹马来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好像刻意在强调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中心的土著国家,其他人都是寄居蟹似的,只要非土著质疑甚至要求更多点权益,就等于是犯了死罪那样的道理。而这样的组织办了分喉舌报,若说《公正之声》不得向非党员销售而遭到禁止,那么这所谓的NGO便得以胆大包天地继续推广它那些极端露骨的言论。
大剌剌的头版便指明了魏家祥侵犯了土著特权,还呼吁请求用内安法令来制裁该者,在这个人人都希望废除毫无人道的内安法令的时期,竟有人还想利用极权的手段来加害于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按照言论自由,我们得尊重土著权威组织的一家之言,问题是,内安法、煽动法等所针对的所谓“危险分子”,试问那些极端鼓吹种族主义的组织到底算不算违法呢?总而言之,马来人特权是动摇不得铁则,非土著相信动则便是触犯了敏感话题,吃亏的非土著却老是遭到恶意的抨击甚至备受羞辱,同样身为马来西亚公民,那非土著的权益谁来保障?差别待遇怎么如此之大?这难道还在围绕着马来人特权问题吗?
魏家祥无非是在奖学金课题上提出看法,就被当作是挑战、威胁马来人特权了,试问谁还会相信有天大马人民真能和平相处,各族之间平等呢?土著权威组织就像是将你一棋似的,叫你别做梦!且看其报的头版,“我们要吃什么?”、“马来人将会消亡”、“槟州马来人特权即将消失”等文章标题,你能相信这是一份“捍卫马来人”的报纸吗?要真是如此,那谁来捍卫所有“马来西亚人”的权益?
有位叫A.B.苏莱曼德开明学者写了篇文章名为《土著权威组织-一个恶魔的再生》里批判了该组织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他性。在它们的信条里,马来人(并非广义上的土著)即等同一切,而促使该组织萌生的原因便是长期主导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马来人特权,这种长期被执政党所利用的工具,已经大大加剧了各族之间的矛盾,使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这还能谈什么种族和谐?种族主义的根深蒂固早已危害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一致之理念,我们还能走多远?像易卜拉欣.阿里这样动不动就想拿人开刀的人物要是持续增多,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好事抑或坏事?
最令人感到气愤的还是该报竟然斥责华文报在搞种族主义(?),这顶高帽还真是犀利,简直把华文报一竿打翻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大毒草”了;然而,为何却又不去控告某“知名”马来文报里的文章有多少曾经触犯了种族主义议题?不妨去拜访一下土著权威组织的主页,那份某主流报纸的广告就打在页面旁,真可谓十足的“中立”且“不偏不倚”。若政府真有心要搞好一个繁荣强盛的马来西亚,我想,是时候该把真正的毒草根除了吧?还等什么呢?又或者,是我们想得太乐观了?还是这根本不太可能实现?


当今大马 7月3日 晚上 8点54分
订阅:
评论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