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在香港,谈民主的人多,谈民智的人少,谈民主与民智关系的人更少。这个现象反映了某些人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居心叵测。
即使你相信民主是普世价值,甚至是放在任何社会都可以造福人民的所谓「universal
good」,也不得不承认「有效、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functioning
democracy)不可能出现于一个充斥着集体愚昧与无知的社会。这其实是常识:你赋予人民当家作主和选贤与能的权利,便要尽其所能,确保他们有能力根
据事实,并充分考虑自身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继而作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你就是把一枝装上子弹的手枪给小孩子把玩。的确,在民主制度表面上最成熟的美国,每年
大大小小的选举之中,也经常出现违反选民自身利益的投票行为(voting against their self-interest)。
这是香港民主发展最大的绊脚石。常言道,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在亚洲四小龙之中,香港对教育的关注最少。教育比民主重要,因为教育是民主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要上街,首先要争取的应该是教育改革;其
次是抗议传媒对香港人填鸭式灌输愚蠢和洗脑。香港人在争取民主的同时不可舍本逐末、倒果为因;但令人感慨的是今日在香港,走上街头以一种指定方式争取民
主,已经成为一条不是对就是错的「是非题」,而非容许你运用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选择题」。说教育比民主重要,更会被标签为一种保守、甚至反动的「政治不正
确」。传媒和政客只谈民主不谈教育,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民主是一出善恶分明、正邪对决的通俗剧,人人都喜欢看;而教育却是一篇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和争取民主,另一方面又无所不用其极地蒙蔽群众和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他们将整
个社会带往「笨下去」(dumbed-down)的方向发展,逐步削弱它实践有效民主的基本条件,最终使它沦为一个不合格的民主社会(unfit for
democracy)。这是从内部打击民主的发展和进程,对民主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下于明目张胆的外部打压。
美国是「民主内伤」的显例。长久以来,在没完没了的意识形态纷争,以及政党、财团、利益团体与媒体无孔不入的操纵下,很多美国人丧失了分辨谎言
与真相的判断力。他们会相信,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九一一」袭击的策划人。总统奥巴马动用数以百亿美元的纳税人金钱拯救濒临破产的银行,但对在投资、退
休金和房地产市场上损失逾十二万亿的老百姓却见死不救。这样一个劫贫济富的总统,在传媒和政敌的口中竟成了社会主义者,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少美国人竟然对
此深信不疑。
凡此种种,显示广泛而深刻的无知与群众愚昧已经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美国作家和前桂冠诗人西米克(Charles
Simic)是其中一个对此深感忧虑的有心人,早前更在《纽约书评》的网页,以《无知的年代》(The Age of
Ignorance)为题,撰文哀悼美国人的民智每下愈况,并指出由于无知的人永远比有见识的人容易宰割,愚弄和瞒骗民众已经成为美国所余无几的其中一项
本土工业。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认为,愚昧可以是一股至为重要的历史力量(Stupidity is sometime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forces)。特首选举期间,三个参选人之中有两个不断被妖魔化,抹黑、栽赃、诽谤、人身攻击和人格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传媒和政客不但没有帮助大众明
是非、辨真伪和分对错,反而往往是这些妖魔化、抹黑、栽赃、诽谤、人身攻击和人格谋杀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同谋。面对赤裸裸、来自四面八方的操纵和支配,
很多香港人都似乎没有抵抗力,而只会随着愚民的指挥棒起舞。再这样发展下去,愚昧迟早会成为香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可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民主跟上帝一样,给予人类行使他们自由意志的权利;而只要让我们选择,我们就有机会选择错误。关键是选民能否从他们
的错误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在下一次选举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坏领袖或其代表的政党说:「滚蛋,你违反了与我们签订的社会契约!」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
优越性在于它有一个内置的自动调节机制,让选民在反复试验和不断摸索之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正因为这个原因,民主的素质跟选民的素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优质
民主,只会产生于一个选民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学习型社会。
林沛理,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及艺术评论小组主席。着有《破谬.思维》、《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书是《反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orum Sosialis tahunan adalah tempat untuk perdebatan dan perbincangan isu-isu kritikal ekonomi dan politik yang memberi kesan kepada rakyat Malaysia. Forum Sosialisme 2011, akan berlangsung pada masa komunisma dan sosialisma digunakan oleh kerajaan pemerintah sebagai “bogeyman” untuk menyerang gerakan rakyat dan juga pengkritik kerajaan.
Tema “Sosialisma sebagai alternatif untuk Malaysia” untuk forum tahun ini ,adalah sangat releven pada masa kini kerana ia menyediakan medan untuk menganalisa sosialisma sebagai ideologi politik dan juga sebagai alternatif kepada sistem kapitalis yang sedia ada.
Banyak negara Latin Amerika sudah pun menerima sosialisma sebagai ideologi pentadbiran , akan tetapi rakyat Malaysia masih mempunyai perasaan was was dan takut terhadap komunisma dan sosialisma yang telah diwujudkan oleh British dan diteruskan oleh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pada masa sekarang. Kini keadaan ini sudah berubah dengan penahanan ahli-ahli PSM dibawah Ordinan Darurat kerana cuba menghidupkan semula Komunisma.
Mulai itu, topik larangan seperti komunisma dan sosialisma menjadi topic perbualan harian rakyat. Maka forum ini memang diadakan tepat pada masanya.
Forum ini akan membantu memisahkan kebenaraan daripada propaganda kerajaan mengenai ideologi kiri.Dalam forum ini akan diperbincangkan sosialisma sebagai alternative walaupun terdapat banyak kritikan terhadapnya.
Sosialisma 2011 akan menyediakan peluang untuk membincang dengan lebih mendalam tentang model sosialis, kelemahan dan kekuatan negara Sosialis yang pernah wujud, ekonomi Malaysia dan bagaimana Sosialisma boleh menjadi alternatif kepada rakyat Malaysia. Forum ini juga menyediakan perbincangan mengenai model ekonomi yang rakyat mahukan.
4 SESI PERBINCANGAN YANG BAKAL DIPERDEBATKAN.
1. Adakah Malaysia maju di bawah Kapitalisma?
2. Adakah Model Ekonomi Sosialis alternatif yang baik ? Kritik mengenai Model Sosialis terdahulu
3. Adalah ideologi Sosialis praktikal dalam masyarakat berbilang kaum seperti Malaysia?
Kebebasan dan pembangunan rakyat yang penuh
4. Sosialisma ala Malaysia?
Ahli Panel
- Dr. Ahmad Fuad Rahmat ( Academician)
- S. Arutchelvan ( Activist and Sec Gen PSM)
- Boon Kia Meng ( Social Activist)
- Choo Chon Kai ( PSM Central Committee and EO detainee )
- Prof. Dr. Edmund Terence ( Academician, University Malaya )
- Jayanath Appudurai (activist – SABM)
- Dr. Jeyakumar ( MP Sungai Siput and PSM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 Melanie Barnes (National Executive, Socialist Alliance, Australia)
- Masjaliza Hamzah(SUARAM & CIJ)
- Dr. Nasir Hashim – Chairperson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 Rani Rasiah ( PSM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 Dr. Rohana Arifin (Chairperson PRM)
- Hishamudin Rais (Former student activist)
- Wan Saiful (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 IDEAS)
Daftar Sekarang
SMS nama anda ke 012-6045807 atau emel ke madhavi3012@gmail.com
Tiket
RM10 (RM5 untuk pelaj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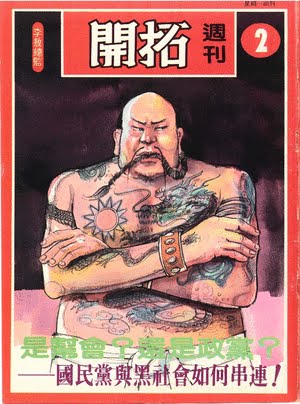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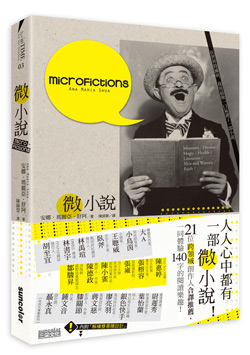
 以前,苏丹依德里斯师训学院是培养渔民和农民子弟的知识中心。师训学院培养出自觉到民族命运的马来精英,他们把殖民者当作是压迫者,几个世纪来奴役马来人。他们起来反抗殖民者。他们是从师训学院教员学习到“马来世界”概念,所以才会有爱国意识和反殖民思想。这些学生接受密集的社会政治学训练,以便民族主义和本土精神在他们脑海中茁壮成长。
以前,苏丹依德里斯师训学院是培养渔民和农民子弟的知识中心。师训学院培养出自觉到民族命运的马来精英,他们把殖民者当作是压迫者,几个世纪来奴役马来人。他们起来反抗殖民者。他们是从师训学院教员学习到“马来世界”概念,所以才会有爱国意识和反殖民思想。这些学生接受密集的社会政治学训练,以便民族主义和本土精神在他们脑海中茁壮成长。 温斯特也希望学院的训练能以效率、经济和统一为基础。学员的课程纲要是与马来学校的课程相接轨。教导的科目有基础农业、手工课、宗教、算术、语言和文学、历史、地理、书法和美术。教导上述科目的教师是有经验的本土教员,也有从英格兰和菲律宾引进的教员。阿都哈迪哈山(Abdul Hadi Haji Hassan)、哈伦莫哈末阿敏(Harun Muhammad Amin)、再纳阿比丁或称为萨巴(Zainal Abidin Ahmad, (Za’ba))和诺丁哈伦(Nordin Haji Harun)都是当年吹响起民族醒觉号角和宣扬爱国精神的佼佼者。
温斯特也希望学院的训练能以效率、经济和统一为基础。学员的课程纲要是与马来学校的课程相接轨。教导的科目有基础农业、手工课、宗教、算术、语言和文学、历史、地理、书法和美术。教导上述科目的教师是有经验的本土教员,也有从英格兰和菲律宾引进的教员。阿都哈迪哈山(Abdul Hadi Haji Hassan)、哈伦莫哈末阿敏(Harun Muhammad Amin)、再纳阿比丁或称为萨巴(Zainal Abidin Ahmad, (Za’ba))和诺丁哈伦(Nordin Haji Harun)都是当年吹响起民族醒觉号角和宣扬爱国精神的佼佼者。 其实,杜塞克(
其实,杜塞克( 阿都哈迪哈山是最早在师范学院掀起该醒觉的最早人物。他在人们眼中是最活跃和和进步的讲师。他以教授历史科栽下民族精神。假如有学生的历史科不及格的话,他会十分生气愤。他认为,历史可观测社会和民族的优缺点,并以日本兴起打败强国俄罗斯来说明这点。很明显的,他在学生中扮演了两个角色,是传授知识的负责任老师和点燃民族醒觉者。
阿都哈迪哈山是最早在师范学院掀起该醒觉的最早人物。他在人们眼中是最活跃和和进步的讲师。他以教授历史科栽下民族精神。假如有学生的历史科不及格的话,他会十分生气愤。他认为,历史可观测社会和民族的优缺点,并以日本兴起打败强国俄罗斯来说明这点。很明显的,他在学生中扮演了两个角色,是传授知识的负责任老师和点燃民族醒觉者。 他能言善辩,导致在1938年时出现学生听完演讲后,大规模集会游行,而且唱着由他谱词的民族精神歌曲,如下:
他能言善辩,导致在1938年时出现学生听完演讲后,大规模集会游行,而且唱着由他谱词的民族精神歌曲,如下: 在之前的师训学院,都是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团结互助、看重社运和民族运动的发源地。但是当萨万被无情的践踏,以及阿当阿德里所受到的不公平惩罚,更让我相信师范大学已经距离从前很远。
在之前的师训学院,都是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团结互助、看重社运和民族运动的发源地。但是当萨万被无情的践踏,以及阿当阿德里所受到的不公平惩罚,更让我相信师范大学已经距离从前很远。 阿兹兰再纳(Azlan Zainal)是2005至2008年前学运分子,任职于独立研究中心(ILHAM)
阿兹兰再纳(Azlan Zainal)是2005至2008年前学运分子,任职于独立研究中心(ILHAM)